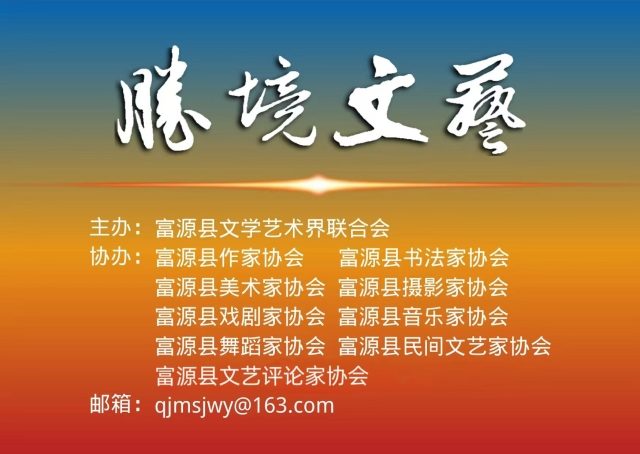住我旁邊的,是一個老人。我只要一翻身,就能看見他。不翻身的時候,也能看見,只是不像現在,看得這么真切。但我根本就不想看他。
我下午剛住進來,他的小孫子就指著腦袋跟我說,我爺爺腦子不太清楚,你多擔待。
一整個下午,他都在嘰嘰歪歪,就像村里那群偷糧食的麻雀,煩人得很。但是,我也好不到哪里去,一躺到病床上,我的腦袋就昏昏沉沉的。我看著天花板,就像看著灰蒙蒙的天空,看不到一小點藍,更找不到一小朵白色的云。我就覺得,我的心里,怕是也住滿了灰色的云。
后來,我就數從輸液管里掉下來的液體。一滴一滴,晶瑩剔透,就像小時候,從屋檐掉下來的雨水。我總會找一只桶,把它們接住。爺爺說,這是天水。是上天的恩賜。田里的莊稼喝了它,就會長得高高的。山中的畫眉鳥喝了它,就會唱出動聽的歌謠。山坡上的那片馬纓花,也會開得紅彤彤的。我們把它燒開泡茶,那味道哇,美!不過,我十多年沒有喝過雨水了。自從下過一場酸雨,沒幾個人敢喝它。
我記性好像不好,數著數著就忘記數到了多少,只好一遍一遍地從零開始數。數到6768的時候,聽到我隔壁床的老人也在數著什么,還有紙翻過的聲音。這時,天早就黑了。我看過去,他眼睛上多了一副老花鏡,手里面捧著一本小冊子,很薄,不知是何物。出于好奇,我伸了下身子。嘿,居然是一本存折。我又伸了伸脖子,身子那側,還壓著好幾本呢。
他將手上的存折向眼睛湊近,開始算數。一萬八了,他嘀咕了一句,笑了起來。但又立馬收起了笑容。他該是發現了我。我立馬平躺下來,看向天花板。在余光中,我還是看見了他,慌里慌張地把存折一個一個放進最里面衣服的兜里,又小心翼翼地扣緊身上的每一個紐扣。做完這一系列動作后,他還小心翼翼地瞟了我幾眼。
我也瞟了他一眼,才把視線收回來。輸液瓶里的液體只剩最后幾滴,我按下床頭的呼叫器。護士很快就來了,說這是今天的最后一瓶,輸完了,感覺怎么樣?我說,我感覺很好。護士拔下我手背上的針管,交代幾句便走了。
我立馬變得清醒,翻了個身,便又看見了老人。他平躺著,喘著粗氣,就像是睡著了一般。我想,他應該是睡著了,不然咋可能這么安靜。我用手撐著床,坐了起來。媽呀,他居然還睜著眼睛,嚇了我一跳。他瞪了我一眼,又警惕起來,用手按住衣服。但好像還是覺得不放心,掙扎著翻了個身,背對著我。他一定是誤會了,以為我在打他存折的主意。我就算得到他的存折,也沒有用,我又不曉得密碼。他也不會憨到把密碼寫到存折上,不是嗎?但是,我該怎么跟他解釋?就算解釋,估計他也不會聽。我只好又平躺了下來,只好又看向天花板。但是,天花板有什么好看的呢。答案是沒有。我已經看了大半天了。不過,不看天花板,我還能看哪樣。
手機。對了,我還能看手機。抖音上那么多美女,夠我看了。我怎么把這個忘記了。雖然一個月前我才把抖音卸載,還發誓,再下載就是王八蛋。但現在,我只能再當一回王八蛋。反正也不差這一回。
我不知道老人是什么時候走出病房的。他和孫子站在病房門口的時候,嚷著要吃米線。我看了出去,他們背對走廊,看樣子是從外面進來的。他們身后是過道,燈亮著,看上去有些昏暗。他的孫子說,這個點,賣米線的,早就關門了。老人指了指房間,這不是還亮著燈嗎?隨后便走了進來,問,這里賣什么?小孫子忙說,這里是病房,你忘了,你就住在這里面。又指了指,那張就是你的病床。你都忘記了。老人說,這里嘛,明明是賣吃的。還指著一個碗問,還有沒有米線?
我想起我的包里還有一些小面包,向老人的孫子使了個眼色,說,米線早就賣完了,只有幾個粑粑。老人說,哪種粑粑?我就把包里的面包拿了出來,說,就是這種。
老人瞅了瞅問,多少錢一個?我說,一塊錢一個。老人說,我買兩個。我拿了兩個面包給他。他立馬喊孫子付錢。吃了一個后,他又問了一遍孫子,錢付了?我連忙說,付過了,用手機付的。
我以為吃完面包,他會消停一會兒。但是,他又拉著孫子走了出去,說,我們再到別的地方看看,我還是想吃米線。
過了好一會兒,他們才又走了回來。老人看了我一眼,說,這里是賣粑粑的,之前來過。去下一家。小孫子也急了,吼了兩句,你到底要整哪樣!這里是醫院,是病房。我要咋個才能跟你講清楚。這個點,我到哪里去買米線。就算你不睡,別人也要睡呀。
護士出現了。她說,我是醫生,你要聽我的話。老人說,我知道你是醫生,我聽你的話。護士扶著他就走了進來,來到床邊,說,那你現在,乖乖地回去睡覺。
老人就乖乖地回到病床上,躺了下來。
但是,護士剛走沒多久,老人又唰的一下坐了起來,將拐杖抓在手里,就下了床。
他的孫子也“唰”的一下從陪護床上坐了起來。揉了揉眼睛,看樣子是才剛入睡。我這才打量起他來,很年輕,估計不到二十。但是,兩個黑眼圈看上去比拳頭還要大。不止一兩天沒有睡好。要是這樣下去,我覺得我也睡不好。
我看了下時間,凌晨兩點多了。
老人向門口走了過來。他的孫子一把將他拉住。老人聲音很大,說,你讓開,我要去礦洞出渣。他的孫子一只手拽住他,一只手推著他的背,把他拉回床上,一把按了下去。老人又坐了起來,不要攔著我,我要去出渣。
值班護士聽到動靜走了進來。拍著他的肩膀說,聽話,快點睡了。這兒是醫院。
老人朝著房間看了一圈,說,你莫要騙我。這里哪里是醫院,這里嘛,是我們礦工的宿舍。該我上夜班了,該我出渣了。你們不要耽擱我。
老人的孫子看了護士一眼,說,現在怎么辦?他年輕的時候在礦洞干過。護士也很無奈,說,只能再想想辦法。不行,就只能給他打鎮靜劑。
這時,老頭兒看向了我。我翻過身,也看向他。他臉上的皮膚向內凹陷,皺紋交叉相錯,就像馬陰山上,那一丘丘縱橫交錯的地。地里面的莊稼剛收割完,一眼望去,顯得荒蕪。不過,冬天一過,這些地里,又會生機勃勃。但是,老人的臉上,卻看不到一點點綠意。
老人開口了,說,馬俊,該出渣了。邊說邊又掙扎著坐了起來。見我沒有動靜,他又喊了一聲,快點。再不起來,又該遲到了。再過一個月就過年了。
我就從病床上坐了起來,說,今晚不上班了。你忘了,今天是周末,調休呢。放假了,今晚可以好好休息。老人嘀咕了幾句,躺了下來,說,放假呀,那就好好休息。天亮了你跟我去鎮上,我寄點錢回家。我說好。
我讓護士趕忙把燈關上。小伙走到我旁邊,說,謝謝你。我擺擺手,說應該的。不然我也睡不著。他怕是把我認成他以前的同事了。
小伙點點頭,說,我爺爺叫馬小國。年輕時在礦山工作,上夜班,負責出渣,干了二十三年。不過,我知道的就是這些。別的他也沒跟我講過。他現在神志不太清楚。東一句,西一句。你不要介意。
我說,不咋個。他以前怕是吃過不少苦,那時候真不容易。
可不是嘛。哪里像現在,生活這么好。不過,也還是不容易。你瞧瞧醫院,到處都是病人。
我也是病人。燒一直退不下來,硬扛了三天才來醫院。不過,醫生說,不礙事,過不了多久就好了。但是,是真的難受,嗓子里就像有一把刀片,整日整夜地割。我咳嗽了幾聲,說,快去睡吧。
我躺在床上,卻睡不著了。小伙子倒是睡得很快,呼嚕聲很快就起來了。我看向老人,他似乎也睡著了,似乎進入了夢鄉。他會夢見什么呢?我想,他肯定會夢見他老婆,肯定會夢見他的兒子。他的兒子,應該上小學了。
我的兒子也在上小學。不過,才五年級,他就開始叛逆,不聽我的話,也不聽老師的話。他迷上了電子游戲,每天放學回來,兩只眼睛就只會盯著電腦。無論我怎么苦口婆心,無論我罵得有多難聽,他那屁股上就像是粘了502膠水,一會兒也不肯離開。好多回,我舉起手,想扇他兩巴掌。但又下不去手。慈母多敗兒,這是古話。但是,他很小的時候就沒有了母親。這么多年,他與我相依為命,我就是他的慈母,根本下不了手。而且,現在是文明社會,動手是不對的。我只能跟他講道理,耐心地跟他講道理。但往往,我講一句,他能回我十句。我也不知道他在學校里,都學了些什么。你說,我那是罵他嗎?我那是恨鐵不成鋼啊。他哪里能體會到我的良苦用心。還說我語言暴力。現在好了,我住院了,他就算是從早到晚都趴在電腦桌上,也沒有人管。又逢周末,肯定開心壞了。這種日子,他怕是盼望了很久吧。
唉!不亂想了。還是睡覺吧。但我翻過來又翻過去,睡眠就是不來找我。我又看向老人,黑漆漆的,只能看出個輪廓。他應該是蜷縮著身子,黑乎乎的一團。呼吸倒是均勻。剛才他說他要去出渣。我想起來,很多年前,離我們兩百多公里的那個鎮上,也有一座銅礦。不過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就停了。聽大人說,那個銅礦邪乎得很,鬧過很多次塌方,死過很多人。后來洞越打越深,又出了多起有毒氣體中毒事故,銅礦廠就徹底停了。我隱約記得,當時銅礦廠給出的答案是,開采難度越來越大,開采成本越來越高,只能暫時停工。但是,在民間也有不少小道消息,有的說,礦洞的下面是個黑洞,不停地吞噬著萬物,已經有人被吞噬了。也有人說,礦洞下面是一座古墓,已經被保護起來了。還有人說,礦洞下面,存在著另一個世界,每天都有聲音從下面傳來,有可能是傳說中的地心人,也有可能是某個被封印的史前怪獸,迫于壓力才停的。這些消息越傳越遠,越傳越邪乎,經過一遍又一遍的發酵加工,就更加離奇,讓你分辨不出哪個是真,哪個是假。但是,有一件事是真的——銅礦廠的人,短時間內,幾乎全離開了這個小鎮。后來,這個小鎮上的很多人也離開了。也間接讓這個曾輝煌過的銅礦小鎮,更加富有神奇色彩。
二十多年過去,這個銅礦小鎮,被開發成了旅游景點。我去過一次。那些青磚砌成的墻上長滿了青苔,房頂的瓦片也長了綠茵茵的草。很多人喜歡來這里拍照,當陽光照過來的時候,給人一種歲月靜好的感覺。但曾經的這里,哪有什么歲月靜好。那些埋于地下的人,有什么歲月靜好。那些為生活賣命的人,有什么歲月靜好。倒是銅礦廠老板,大賺了一筆,走了。現在又回來,再賺一筆。受苦的,都是那些身處底層的人。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夠記住他們。
(節選,全文刊載于《廣州文藝》2025年第12期)
【作者簡介】
李世發,筆名木非可。1992年生,云南大姚人。有中短篇小說發于《解放軍文藝》《四川文學》《廣州文藝》《湘江文藝》等刊物;有詩歌發于《人民文學》《十月》《文藝報》《作品》等刊物。入選《十月》雜志第十二屆全國詩會。
來源:廣州文藝
編輯:詹宇涵
審核:盧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