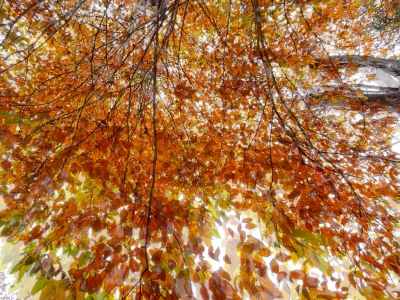又到小鳥天堂
一棵榕樹與一個世紀的對話
文○梁慶才
 ?
?
到了小鳥天堂,看的不是鳥,而是樹。
三十年前,為了瞻仰梁啟超故居,我初次來到廣東新會。那時并不知道,與梁啟超故居僅三公里之遙,還藏著一處“小鳥天堂”。記得當時只有一棵巨大的榕樹,慢慢衍生出十幾畝的榕樹林,靜靜立于水圍之中。老鄉劃著小船,載著我們穿行在榕樹的根須間,遮天蔽日的樹蔭擋住了南國的炎熱,船槳劃水聲與老鄉講述的巴金故事交織在一起,恍如隔世。
 ?
?三十年后,我與友人余向強站在廣東中山的陽光下,我提議再去小鳥天堂。他愣了一下:“梁老師這是故地重游啊,中山有好多好地方都沒帶您去,為何要再去看小鳥天堂?”我說:“因為巴金都去過那里兩次呢 ,我們多去幾次何妨?”
于是,我終于踏上了這次尋找記憶的旅程。水圍依舊,榕樹更茂,只是游船不再穿行其中。
從“雀墩”到濕地公園
 ?
?抵達小鳥天堂已是下午三點。車被遠遠攔下,不再能直開水邊。原來,這里已擴建成占地數千畝的濕地公園。園內榕樹林立,亭臺錯落,木棧道蜿蜒。我們走了許久,卻找不到記憶中的那株榕樹和水圍子。詢問游人方知,真正的小鳥天堂還需往深處走。
 ?
?終于,那個水圍子映入眼簾,榕樹的根系比三十年前更加茂密,已不允許船只進入。我們只能隔水相望,再也無法重演當年穿行其間的愜意。老鄉的小船和故事,已成為遙遠的記憶。
我看到了“巴金亭”,還有刻著巴金文章和語文課本模樣的雕塑,專門供游人拍照留念。站在雕塑前,我沉思良久——假如沒有巴金的那篇散文,這里還會是今天的模樣嗎?
一棵樹與一位作家的相遇
 ?
? 時光回溯到1933年。未滿30歲的巴金應朋友邀,來到新會天馬鄉。一個傍晚,在友人的陪伴下,他劃船繞游當地人稱“雀墩”的沙洲。巴金在文中寫道:“我仿佛聽見幾只鳥撲翅的聲音,但是等到我的眼睛注意地看那里時,我卻看不見一只鳥的影子。”那晚,他帶著些許失望離去。
第二天早晨,當巴金前往茶坑鄉探訪梁啟超故居時,再次經過“雀墩”,卻看到了令他驚嘆的景象:成千上萬的鳥兒在榕樹間飛舞頡頏。他在文中生動地描繪:“到處都是鳥聲,到處都是鳥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飛起來,有的在撲翅膀。”
回到上海后,巴金懷著對這一幕的美好回憶,寫下了《鳥的天堂》這篇散文。文中那句“這美麗的南國的樹”和最后的感嘆“那‘鳥的天堂’的確是鳥的天堂啊!”讓這個原本只是當地風水樹的“雀墩”一躍成為天下聞名的“小鳥天堂”。
而“小鳥天堂”這個名字的由來,也有一段趣事。據記載,在巴金散文發表后的一次討論中,有人指出“鳥的天堂”中“的”字是普通話,廣東人不習慣,建議改稱“小鳥天堂”,“小鳥”通俗雅致,因此傳開。
四百年的根脈奇跡
 ?
? 我想去找當年的船工,可我連村莊都也找不到了。水邊碰到一個年長者,顯然常來這里看樹或者是看鳥。他告訴我說,小鳥天堂里的這棵榕樹本身就是生命的奇跡。四百多年前,天馬村人為防范水患,在河口沉下一艘沙船,筑成沙洲。傳說一個挑沙船工隨手將榕樹枝做成的扁擔插在沙洲上,這根榕枝竟生根發芽。
他還告訴我,榕樹遇土則活,向水而長。枝干生出氣根,氣根觸土變成新樹干,又抽枝發芽,長成新樹,新樹再長氣根。如此循環往復,一棵榕樹變成了一片榕樹林。如今,這個龐大榕樹家族覆蓋面積已達20畝,蔚為壯觀。
長者說,村民視榕樹為“神樹”、鷺鳥為“神鳥”,立下嚴明鄉規:若有上島擾鳥、傷鳥者,皆以褻神者大逆不道治罪。這種呵護生命、熱愛自然的價值觀已融入當地人的生活血液。
文化符號與自然保護的辯證
 ?
?站在巴金亭前,我不禁思考:假如沒有巴金的那篇文章,假如這篇文章沒有入選小學語文課本,小鳥天堂會是怎樣?
在巴金到訪之前,“雀墩”雖已有數百年歷史,卻鮮為外人所知。甚至到上世紀50年代末,天馬村民仍習慣稱其為“羅星凸”或“雀墩”。1958年,廣東省領導來此考察后,才開始建設小公園。而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1978年,《鳥的天堂》被收入小學語文教材后,億萬兒童的誦讀讓小鳥天堂名揚天下。
文化的加持使一棵樹蛻變成一個文化符號。巴金的文章為這片自然奇觀注入了靈魂,而教材的傳播則讓它成為全民共享的文化記憶。1982年和1986年,巴金兩次親筆題寫“小鳥天堂”,為這片景觀奠定了永恒的文化根基。
 ?
? 在巴金的“小鳥天堂”原文石刻前,我在想,有時候,一段文字特別是名家的文字敘事對一地文化傳承、傳播和保護是多么的重要、多么有趣啊!
然而,保護與體驗之間似乎又存在著永恒的辯證。三十年前,我能乘船深入榕蔭深處,親近自然,卻也意味著保護措施的缺失;三十年后,完善的設施保護了生態系統,卻失去了與自然親密接觸的體驗。
這種得失之間,或許正是現代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縮影吧。
不變的天堂之歌
 ?
? 臨別時,我回頭望向那片榕樹林。雖然無法再乘船穿行其間,但鳥兒依然在樹上棲息飛舞,延續著自然的頌歌。當地居民與榕樹之間那份古老的契約以新的形式在延續——保護范圍從最初的15畝擴大到今天的4100多畝,從一棵樹變成了一片濕地公園。
有些東西變了,有些卻始終未變。 變的是保護的方式和規模,不變的是人對自然的敬畏;變的是游客的體驗形式,不變的是這片土地的生命力。巴金當年感受到的那份祥和寧靜而又生機勃勃的氣息,依然在每一片榕樹葉間流淌。
歸途中,我想起田漢1962年到訪時留下的詩句:
三百年來榕一章,濃蔭十畝鳥千雙。
并肩只許木棉樹,立腳長依天馬江。
新枝還比舊枝壯,白鶴能眠灰鶴床。
歷難經災從不犯,人間畢竟有天堂。
 ?
? 是的,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無論保護方式如何更新,這片小鳥天堂始終守護著自然與人文相融合的奧秘。而巴金的故事,也如同那榕樹的氣根一樣,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延續著一個關于生命、文學與守護的永恒傳說。
當我們驅車離開時,夕陽西下,余暉灑在濕地公園的水面上。或許,今日的小鳥天堂已不是我記憶中的模樣,但它正以另一種形式,繼續書寫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故事。
作者簡介:
 ?
?梁慶才,資深媒體人,軍旅作家,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長期從事軍事新聞宣傳,多次參與組織、策劃全2國、全軍重大典型宣傳。著有長篇報告文學《風雨太平洋》《實證陳儼》《跨越大洋的握手》《聲渡遠灘》等。代表作長篇報告文學《時代答卷—來自一個國家級貧困縣的脫貧攻堅報告》獲河南省第三屆優秀報告文學特別獎、河南省第十三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新近創作出版的中國第一部未成年人保護長篇紀實文學《以國家的名義——中國未成年人司法保護調查報告》受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全程支持,被媒體和專家學者定位為“中國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里程碑式記錄”,在全國引起廣泛關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