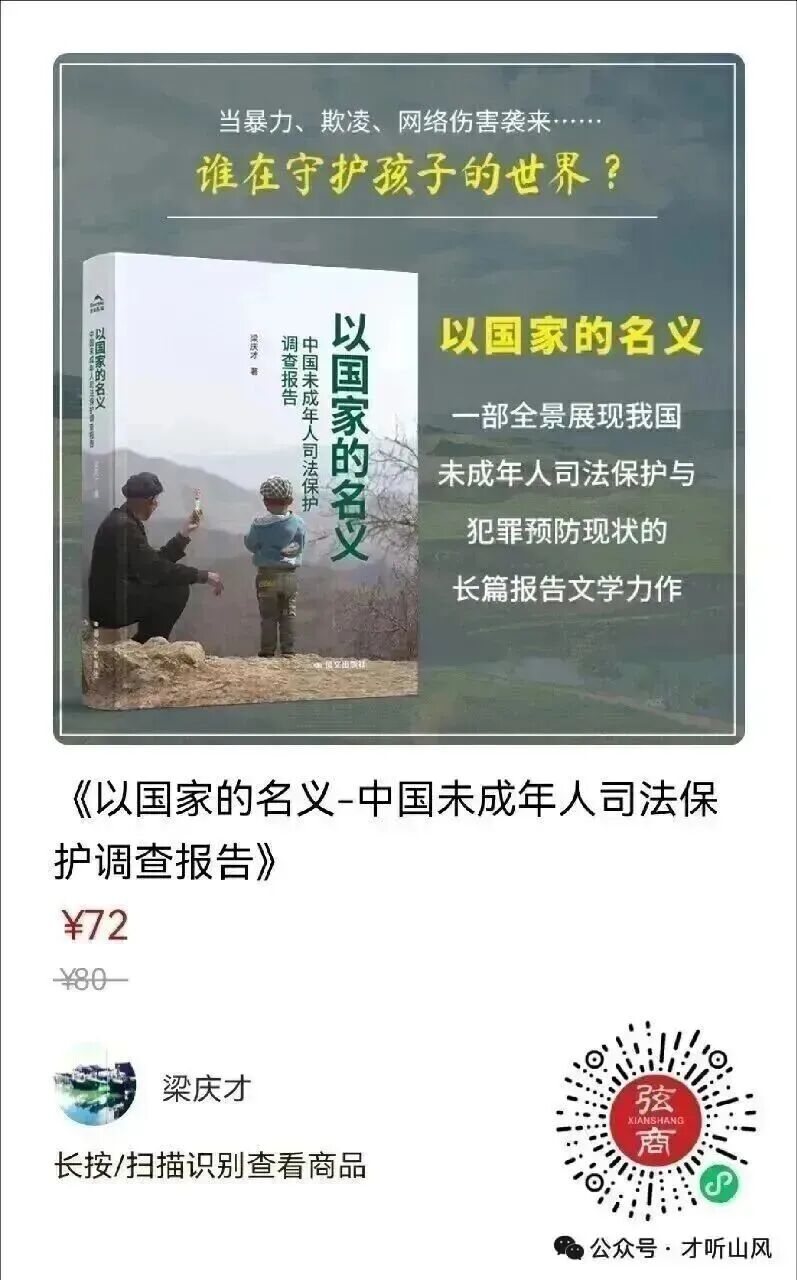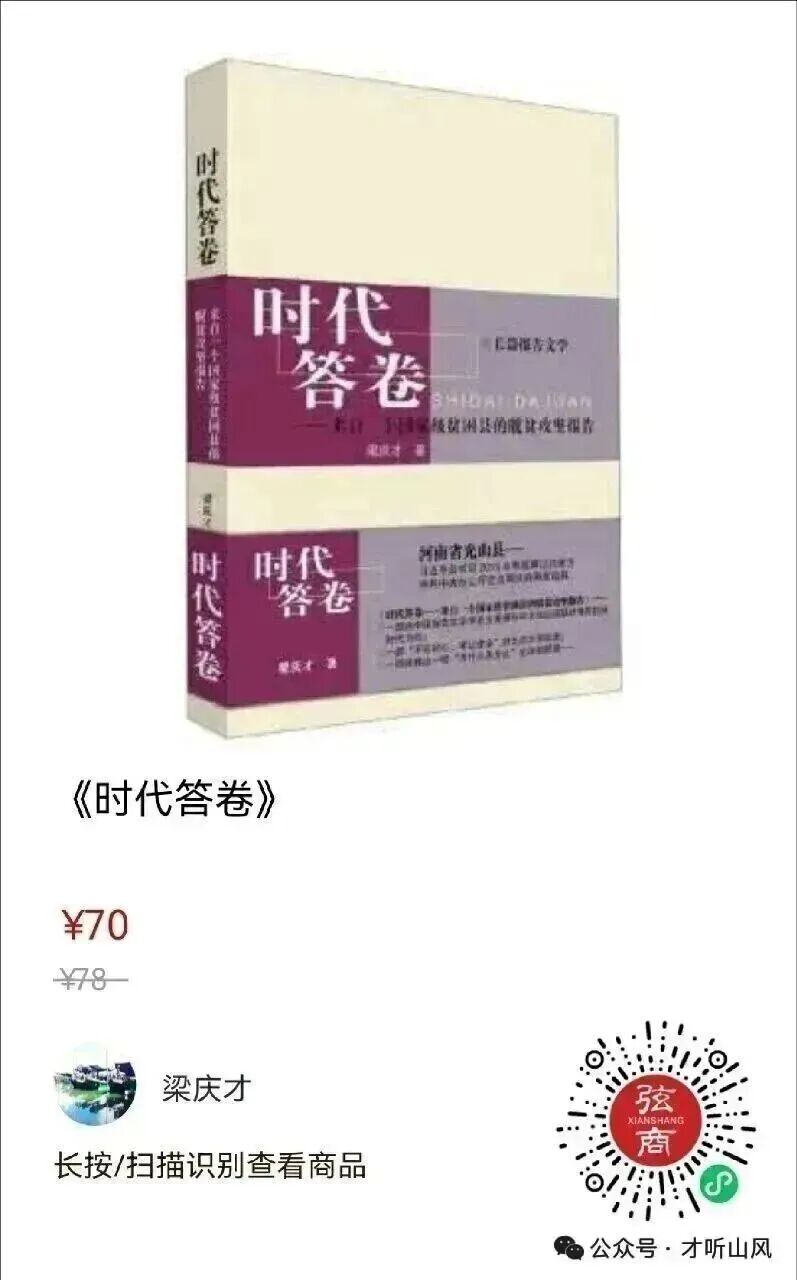琴臺寂寂有清音
一位旅人的江城尋訪記
文□梁慶才

緣起:不尋名樓,獨訪幽臺
許多人到武漢,總為黃鶴樓的雄渾或東湖的浩渺所動,而我屢次踏足江城,心頭卻總縈繞著龜山西麓、月湖東畔的一處小園——古琴臺。它不似黃鶴樓般游人如織,亦無東湖的煙波壯闊,僅以一方漢白玉石臺、幾段碑廊、一闕“高山流水”的舊夢,靜候著懂得“尋音”之人。最近的一次是陪我的老恩師、從廣東汕頭電視臺副臺長任上退下來多年的“杜臺”杜煥壯,此番重游,我們刻意避開了喧囂,擇一個雨后清晨,沿湖踱入這片僅占地十五畝的園林,試圖在粉墻黛瓦間,觸碰那段穿越千年的知音絕響。
故臺新雨:細節里的歷史余溫


“杜臺”喜歡拍照,而我喜歡尋詩。行至院落中央,漢白玉筑成的琴臺靜臥于蒼松翠柏間。石欄板上“伯牙摔琴謝知音”的浮雕已被歲月磨出溫潤光澤,撫過凹凸的刻痕,仿佛能聽見裂帛般的斷弦之聲。一旁碑廊中,嶺南才子宋湘的竹葉題詩尤為動人:“噫嘻乎,子期知音,何以知在高山之高,知在流水之深?”
“杜臺”在碑廊駐足良久,與我說,束竹為筆的狂放墨跡,竟將知音難覓的千古悵惘,凝作石上永恒的叩問。
知音之思:從傳說照見人間


轉過身來, 最妙的是一處名為“知音樹”的奇景。一株古木竟分為兩枝,交錯生長,宛若伯牙與子期的魂魄相依。樹下懸著無數“知音鎖”,鎖上刻著游人的心愿。我見一少女悄悄掛上一把銅鎖,低聲對同伴說:“愿我們像伯牙子期,縱使天涯,心音相通。”——原來,知音文化從未死去,它只是化作了尋常人對真摯關系的渴望。
駐足“知音樹”,“杜臺”似樹沉思不語。
靜思與回望:于寂靜處聽驚雷

離園前,我陪“杜臺”坐在“伯牙亭”中望月湖,邊說著我、我們和老師宋樹根之間的故事。雨已停歇,湖面如鏡,倒映著對岸琴臺音樂廳的現代輪廓。古今光影在此交錯,我恍然頓悟:古琴臺的真意,不在復原歷史,而在喚醒每個來訪者心中對“知音”的珍視。正如一位游客所言:“這里的美好,藏在亭臺布局里,可觸可感。”
與老恩師對坐伯牙亭,我暗自思忖,若說黃鶴樓是江城張揚的詩篇,古琴臺便是默誦的偈語。它提醒我們:“知音不在遠方,而在傾聽的勇氣;知音文化不在典籍,而在尋常人相知相惜的瞬間。”
離臺時,我回望“高山流水”匾額,忽覺這四字不僅是琴曲之名,更是一種生命境界——唯有心懷高山之志、流水之柔,方能在喧囂塵世中,識別靈魂的共鳴

后記:二O二五年的這個冬日,我路過江城武漢,再次重訪古琴臺,發現這里已與龜山、月湖、晴川閣整合為“知音文化旅游區”,新增電子古琴互動、雅集沙龍,讓千年故事“活”了起來。但于我而言,它最動人的仍是那份“寂寂中的回響”——如伯牙碎琴后空谷余音,提醒著每個現代人:在效率至上的時代,仍該為心靈留一方“聽琴”的凈土。
這一日,我買下三枚竹葉書簽,上刻“萬古高山,千秋流水”,一枚留給自己,另兩枚分寄給“杜臺”和老師宋樹根。杜臺回信:“見簽如面,恍如昨日。”樹根老師早年在海軍南海艦隊文藝創作室主任任上,曾脫產在武漢大學作家班深造兩年,他回我說,或許,真正的知音,是與另一個自己相遇;而古琴臺,正是江城贈予浮世旅人的一面澄明之鏡。
再次回望古琴臺,我心生一念:風雨半生,后續,我得寫一篇關于我與“杜臺”與老師宋樹根的故事。
(配圖 杜煥壯)
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