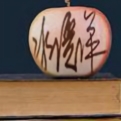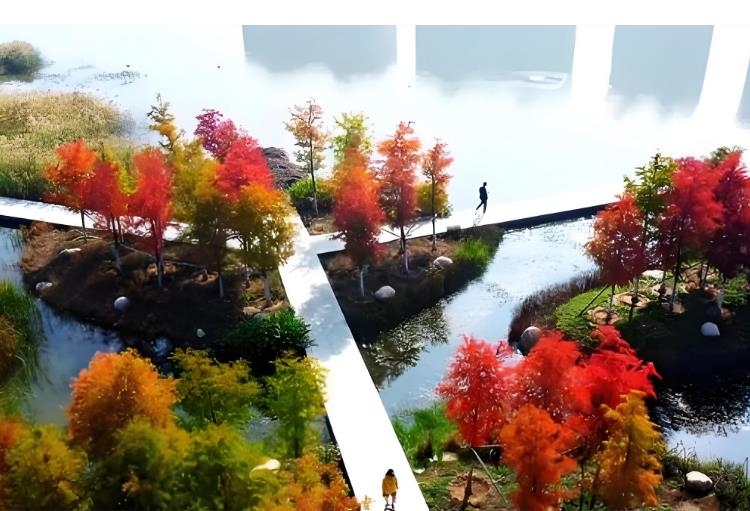
漂泊的聲音
#創作挑戰賽十一期#
駐馬店這里的夜色,確是很美的。不是那種濃得化不開的、沉沉地壓在眼皮上的美,倒像是一大碗沖得極淡極薄的藍靛,從天上漫漫地、無聲地傾瀉下來,將天地萬物都柔和地浸泡在里面。遠處的幾盞街燈,便成了這碗靛青湯里化不開的、幾小滴溫潤的油彩,光暈朦朦的,有幾分可憐可愛的模樣。風是有的,只是極輕,極緩,拂在臉上,像舊情人涼而滑的指尖,帶著說不清的惆悵。
就在這時,那聲音便來了。
起先只是一縷,游絲一般,仿佛是從那最濃的夜色背后,或者是從記憶的極深極遠處,怯怯地探出頭來。隨即,便多了起來,一縷,又一縷,交織著,纏繞著,漫了過來。說是“漫”,是再貼切不過的。它不像雨,有那淅淅瀝瀝的、實在的形體;也不像風,能教樹葉簌簌地應答。它只是“漫”,像一種無形的流質,貼著地皮,沿著墻根,悄沒聲息地,將這夜的美,一點一點地濡濕了,滲透了。這便是漂泊的聲音了。
這聲音里,有火車的汽笛,拖著長長的、疲憊的尾音,從一座陌生的城,劃向另一座陌生的城;有輪船沉郁的悶響,在無邊的海上,吐著咸腥的、寂寞的泡沫;有機場廣播里那永遠標準而又疏離的女聲,一遍遍催促著啟程與告別。更多的,卻是些不成片段的、細碎的聲響——是旅社里,隔壁傳來的一聲模糊的咳嗽;是小酒館里,杯底與桌面那一聲清脆又寂寥的碰撞;是異鄉的雨夜,雨水敲打窗欞,那不急不緩的、無盡的獨白。
這些聲音,它們沒有家。它們從生命的這一站,漂浮到那一站,像些失了根的水草,在時間的河流里,無可奈何地搖曳。它們彼此碰撞,又彼此疏離,共同匯聚成這一片浩大而又虛無的聲之海,在這美麗的夜色里,低低地回響。
我的鼻子忽然一動。是一種香氣,一絲極幽微,又極執拗的甜。我抬起頭,循著那氣味望去。啊,原來是墻角那株老梔子,不知何時,已悄悄地開了滿樹。花朵是那種笨笨的、毫無心機的白,在墨綠的葉叢里,顯得有些不諳世事的天真。那香氣便從那里來,一絲絲,一線線,在沉靜的夜風里,織成一張看不見的、溫柔的網。
“你是否聞到,頭頂的梔子花開了?”
我幾乎要脫口問出了。可是問誰呢?四周只有那漂泊的聲音,依舊在漫著,漫著。這花香,與那聲音,是多么不調和的兩樣東西呵!一個那樣切實,那樣飽滿,帶著泥土的憨厚與生命的熱情;一個卻那樣虛空,那樣無著,是剪斷了纜繩的舟,永遠在尋找那不可能的岸。然而它們此刻,偏偏就在這同一片夜色里,相遇了。花香仿佛要給那虛無的聲音一個形體,而那聲音,又仿佛在訴說著花香終將凋零的宿命。
于是我想起了你。你的聲音,便也像這漂泊的聲音一樣,在許多年以前,就這樣漫過我的生命。
那也是在夜里,在沒有人群的地方。你說,人群是健忘的,他們的熱鬧,像潮水,來得快,去得也快,最后只在沙灘上留下一些空洞的貝殼。你寧愿在沒有人的地方,讓自己的聲音,像一朵奇詭的花,獨自盛開。是的,一年又一年,你的聲音,就在那沒有人群的、我心靈的曠野里,固執地盛開著。那聲音,有金屬的質地,冷靜,而清醒;卻又帶著一種奇異的溫暖,像冬夜里,一點將熄未熄的爐火。
因為這聲音,這個城市,在我眼里,也便失去了它固有的、沉重的記憶。那些標志著歷史的碑石,那些訴說著過往的建筑,都仿佛褪了色,成了舞臺上千篇一律的布景。它們不再能壓迫我,不再能用它們那龐大的“曾經”,來質疑我渺小的“現在”。只有這夜色的美,是真實的;只有你的聲音,在這美里回蕩,用它那漂泊不定的軌跡,用它那永不棲息的姿態,詮釋著一種生命的、悲愴的張力。
你是不屬于白天的。白天是屬于眾人的,屬于規則、勞作與喧囂的。白天的滋味,是油鹽醬醋,是得失盈虧,是實實在在的,可以被咀嚼,被吞咽,被消化的。而你,是沒有咀嚼過這白天的滋味的。你的世界,在太陽落山之后,才真正地蘇醒。你的食糧,是孤獨,是思想,是這無邊無際的、美麗的夜色。
忽然覺得有些冷了。是那漂泊的聲音,帶著夜深的涼意,漫到了我的骨子里。我轉身回到屋里,擰開那盞昏黃的舊臺燈。光暈灑下來,在桌面上圈出一小片溫暖的、與世隔絕的疆域。我拿起那只素白的瓷杯,里面還有小半杯未飲盡的酒。酒液是琥珀色的,在燈下漾著一種內斂的光華。
我舉起杯,并不為邀誰共飲,只是默默地,對著窗外那無邊的夜,對著那夜中漫著的、你的和我的漂泊的聲音,輕輕一舉。
在春天即將來臨之際,飲一杯酒,暖暖身子罷。
春天,總是要來的。帶著它的花紅柳綠,它的生機勃勃,它的、屬于所有人的希望。但那,終究是明天的事了。今夜,且讓我守著這片被聲音濡濕的夜色,守著這縷執拗的梔子花香,守著那在記憶深處永不凋謝的、你的聲音。
我將杯中那點暖意一飲而盡。一股熱流,從喉間直落到胃里,然后慢慢地,向四肢百骸擴散開去。身子果然暖了些,雖然指尖,依舊還是涼的。
那么,便繼續罷。
繼續在這美麗的,讓人想笑又想哭的夜里,漂泊。
(使用“DeepSeek”改寫張廣智原創詩歌。圖片來自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