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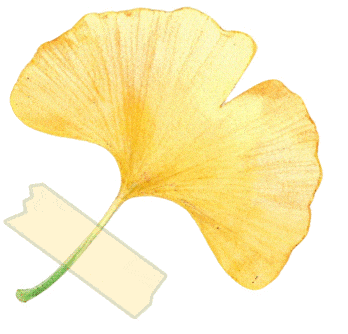
神池是晉西北最高最冷的縣。三月里的一天,我來這里是為了訪問一個鄉村女教師。她的事跡很簡單:在一盤土炕上教書已二十五年。一個年輕女子,隱居深山,盤腿坐炕,一豆青燈,幾個頑童,二十五年。這是何等清貧堅忍的煉丹修道式的生活啊,我一定要去看看。
車子進了山,翻上山頭,早沒有了路。風像刀子一樣專找著領口、袖口往里鉆。山上除了殘雪,就是在風中抖動的、如鋼絲一樣的枯草莖。
步行轉過一個山坳,村口的第一個院子就是學校,傳出了孩子們清脆的讀書聲。我們剛踏進院子,一個中年婦女在窗玻璃上一閃,急忙迎了出來。她就是炕頭小學的女教師賈淑珍。炕頭上分三排盤腿坐著十三個孩子。一個個瞪著天真的眼睛,看著我們這些山外來客。炕下放著一溜小棉鞋。炕對面的椅子上靠著一塊小黑板,上面寫著漢語拼音。賈老師迎進我們說:“天這么冷,好辛苦,快炕上坐。”一邊讓孩子們往炕里擠一擠。山里的冷天,家里最暖和的地方就是炕頭,如同賓館會客室里的正席沙發,是專讓貴客的。我們不愿打擾小窯洞里的教學秩序,不肯上炕,她就讓我們到她的窯洞里。
“那是一九六一年,十七歲,我初中畢業,和張亮結了婚,來到這個村。全村不到二十戶,沒有學校。八九個娃娃,不是在村里爬樹,就是在地里割莊稼。我跟支書說,我念書不多,總還能看住個娃娃吧,比他們在村里撒野強,當時隊里沒有窯洞,我剛結婚,就把學校搬到了我的洞房里。”
“我把家里的殺豬案板洗了洗,刷上炕洞煙當黑板,又把山上的白土碾成面,和上山藥蛋粉搓成條,就是粉筆。沒有書,就回到娘家村里借。”
賈淑珍坐在炕邊,像敘家常,追憶著往事。話里并沒有多么崇高的理想,也沒有多么宏偉的計劃,更沒有什么壯烈的舉動。一切都順乎自然,村里的娃娃沒人管,自己就當看娃的,野慣了的孩子,撕了窗戶,扯了炕席。地下,雨雪天兩腳泥;冬天燒炕還要出去打柴、接草。同一盤炕上四個年級,有的上算術,有的上語文,有的愛打鬧,有的膽小不敢說話。她都靠自己無私的心和慈母式的情,把這批野孩子帶大一茬又一茬。只在那花燭洞房中的土炕上,就送走了十二茬學生。全村三十五歲以下的無不是她的學生。
土炕,這盤熱烘烘的土炕,就是憨厚的北方農民一個生存的基本支撐點,是北方民族的搖籃。在這盤土炕上,人們睡覺、吃飯、紡線。晚間又常擠到炕頭上說古拉家常。這九尺炕頭便是他們的生活舞臺,世代他們就這樣繁衍、生存、進步,而賈淑珍又在舞臺上加進新的內容——教育。人呱呱落地,來到這炕上,不該光吃、睡和干活,還應該有文化有精神文明。這個普通的女教師,給炕賦予了新的含義。
二十五年了,在這盤土炕上,他們連同自己的,共帶大了四十二個孩子。我問:“張亮現在干什么?”
“他在十五里外的一個村里教書。”
“你為什么不和他調到一起?”
“我們這個村小,他回來吧,用不著兩個;我去他那村吧,一走,學校也就停了。現在雖說有了窯,可誰想來呢?直到去年才通了電。”
別人不愿來,她卻舍不得走。事情總得有人干,是苦是虧總得有人吃。自覺奉獻,自覺犧牲,這就是她的人生哲學,平靜而自然。
我們就這樣不緊不慢地拉著話,隔著光線,我端詳一下她的臉,已爬上不少皺紋。我計算她今年該是四十四歲,可她至少像五十多歲。多年為人師表的嚴肅和山里生活的清苦,塑造了她這種謙虛、誠實、任勞任怨和略顯憔悴的身影、風度。我心里只是莫名地為她惋惜和不平,但說出口的卻是這么一句:“山里生活這么多年,身子骨還好吧。”
“好甚哩,六年前檢查說是肝炎。進城打了個方,回來連吃了四十服,就再沒去看。離不得,一進城少說也得七天,誰代課呢?山里人,身子能扛呢。”
我看看表,已近中午,便要起身告辭。她還是堅持要我們吃了午飯,我們趕緊逃了出來。
告別時,我還是提醒她要看病,她卻一直念著,來了一趟,飯沒吃一口,你們衣裳單,別著涼。村民們的話又響在我耳旁:“賈老師,好人哩。”這樣的好人真不多啊,像一棵靈芝草,靜靜地藏在深山里。這個二十戶的小村托了她的福啊!幾十年來,有了一個她,全村就沒有一個文盲,還出了兩個大學生。都說教師是蠟燭,她就是這樣默默地燃著自己,在這無人知曉的山里,在那盤農家最普通的土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