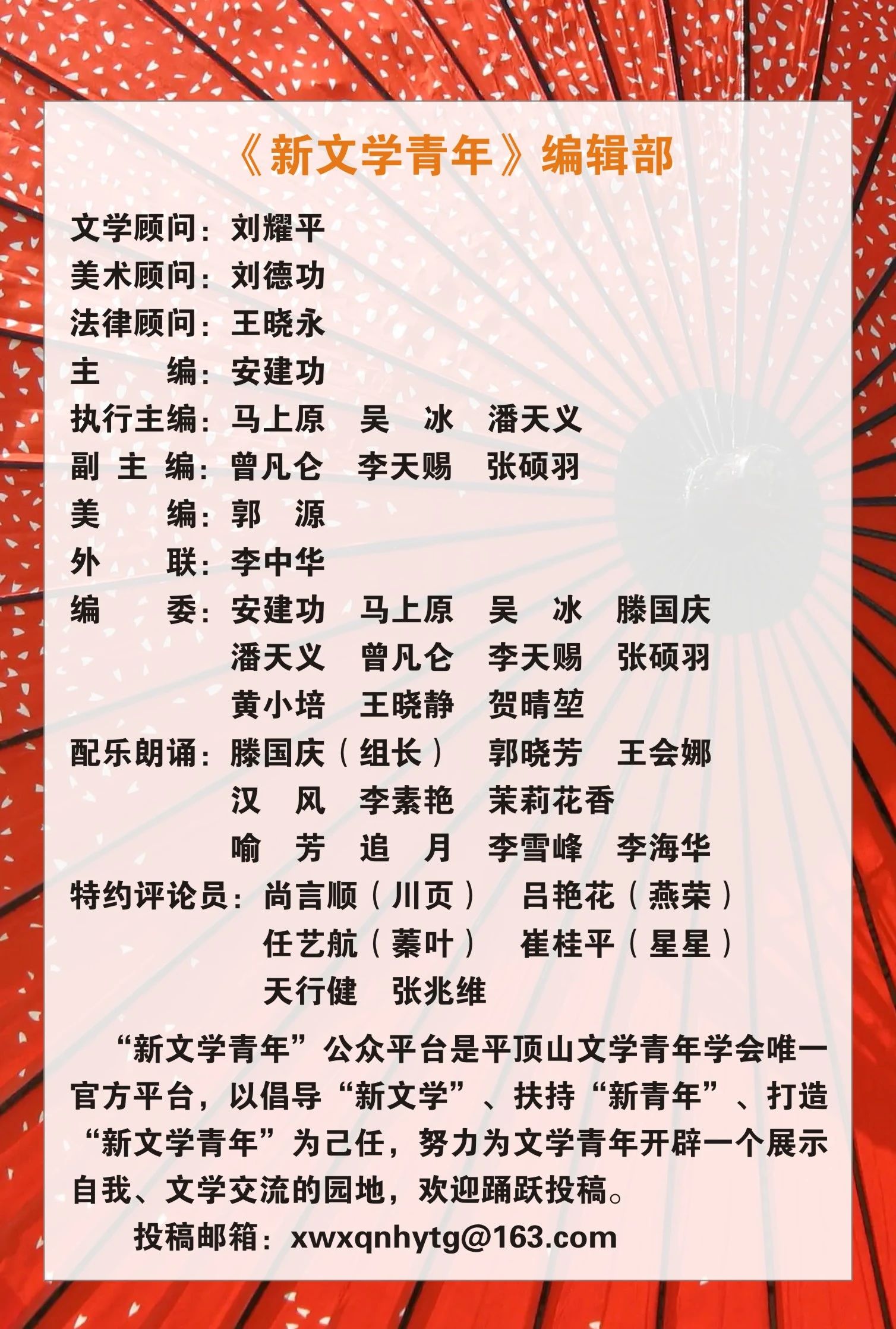1780期 主 編:安建功
執行主編:李天賜
第八屆“鐵荷”主題大賽征文
秋風掠過豫中平原,卷起路邊的枯葉,也卷起我心中層層疊疊的鄉愁。再次踏上歸鄉的路,腳下的柏油路寬闊平坦,取代了當年坑坑洼洼的土路,可心里那份熟悉的親切感,卻淡了幾分。

咱打小住慣的村莊,如今就像個陌生的故人,站在原地,任時光雕琢,早已沒了舊時的模樣。
看著村莊一天天變樣,心里真是五味雜陳。新蓋的小樓拔地而起,替代了低矮的土坯房;太陽能路燈照亮了村道,取代了當年昏黃的煤油燈。
這些變化,本該讓人欣喜,可每當看到那些熟悉的老房子被一一拆除,磚瓦散落,心里就像被什么東西揪著似的難受。
那些老房子里,藏著咱多少童年的記憶啊!
春天,在院子里的老槐樹下追著蝴蝶跑。
夏天,搬個竹床躺在門口,聽爺爺講古往今來的故事。
秋天,在屋檐下幫著爹娘晾曬玉米和花生。
冬天,圍著灶臺烤紅薯,聞著那香甜的氣息,心里暖烘烘的。
如今,老房子沒了,這些記憶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不知道該往哪兒擱。

村里的嗩吶聲又響起來了,尖銳的調子硬生生劃破了村莊的清靜,聽得人心里直發慌。這已經是今年第幾回了,我都記不清了,每回這聲音一鬧,就知道又有人沒能熬住日子,永遠留在了從前。記得上個月,村東頭那位老爺子走了。他被病痛纏磨了好幾年,走的時候瘦得只剩一把骨頭架子,半點沒有當年在村口蹲坐下棋時的硬朗勁兒。他那白發蒼蒼的老兩口,抱著他的遺體哭得肝腸寸斷,一遍遍地喊:“娃啊,再讓爹娘好好看看你!” 那聲音,聽得人鼻子發酸,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 還有前陣子,村西頭的老奶奶壽終正寢,活到了九十三歲,子孫滿堂,按說算是喜喪。可當哀樂一響起,她那小孫子指著墻上的照片,拽著大人的衣角,放聲哭道:“我要奶奶,我要奶奶抱我!” 那一刻,在場的人眼圈全紅了,再熱鬧的排場,也掩不住那份生離死別的悲傷。 白布條、白帆在秋風里晃來晃去,像一個個蒼白的嘆息。嗩吶聲吹得悲愴又凄厲,每一個音符都往人心尖上戳,攪得人心里揪著疼。可再響的嗩吶聲,也蓋不住靈堂里撕心裂肺的哭聲。原來,在生離死別面前,再剛強的人也會卸下偽裝,眼淚說掉就掉。

以前,在村口的大槐樹下,總能看到一群老人扎堆嘮嗑,東家長西家短,笑聲不斷;每到飯點,家家戶戶的煙囪里冒出裊裊炊煙,灶臺上飄出陣陣飯菜香,那是家的味道,是煙火人間的溫暖。可如今,這些畫面都成了再也回不去的昨天,只能在記憶里一遍遍回放。
在外頭飄了這么多年,走南闖北,苦的甜的都嘗遍了,才明白最牽掛的還是這個小小的村莊。累了、倦了,總會想起家里的一切。想起小時候,娘在耳邊絮絮叨叨的叮囑,雖然當時覺得煩,可現在想來,滿是溫暖;想起家里的煙囪冒出的裊裊炊煙,那是最美的風景;想起村頭那條彎彎曲曲的小路,小時候背著書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學,路上總能碰到端著碗蹲在門口吃飯的鄰居,熱情地招呼一聲,嘮上兩句家常。那些平淡又溫馨的日子,是我心中最珍貴的寶藏。
可這回真的走在村里的小路上,眼前的景象卻讓人心寒。曾經熱鬧的村莊變得冷冷清清,只剩下斷墻殘壁,一間間破舊的房屋鎖著生銹的鎖,門上的春聯早已褪色,露出斑駁的痕跡。院子里的雜草長得比人還高,似乎在訴說著歲月的滄桑。當年家家戶戶飄出的飯菜香,變成了如今的寂靜無聲;當年村口的歡聲笑語,變成了如今的鴉雀無聲。以前那些熱熱鬧鬧、暖乎乎的日子,現在都變成了再也醒不來的夢。

夕陽西下,余暉灑在村莊的土地上,給斷壁殘垣鍍上了一層金色。我站在村口,望著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心里滿是惆悵。故鄉是根,無論走多遠,都忘不了那份牽掛。可故鄉的變化,卻讓這份牽掛多了幾分苦澀。那些逝去的人,那些消失的老房子,那些難忘的歲月,都成了心中永遠的念想。只愿這份鄉愁,能化作對故鄉的祝福,希望它在變遷中,能留住幾分舊時的溫暖,讓漂泊的游子,還有一處可以安放心靈的港灣。

周軍輝,河南葉縣人。系葉縣作家協會會員,《夏李記憶匣》總編,天津開放大學家庭教育學院特聘講師。其作品散見于《平頂山日報》《葉縣視界》《新鄉土文學》《智泉流韻》《澧水文學季刊》等多家媒體平臺。素喜翰墨,心篤文學,常以筆為楫,于文字滄海中溯游求索,打撈生活意趣與時代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