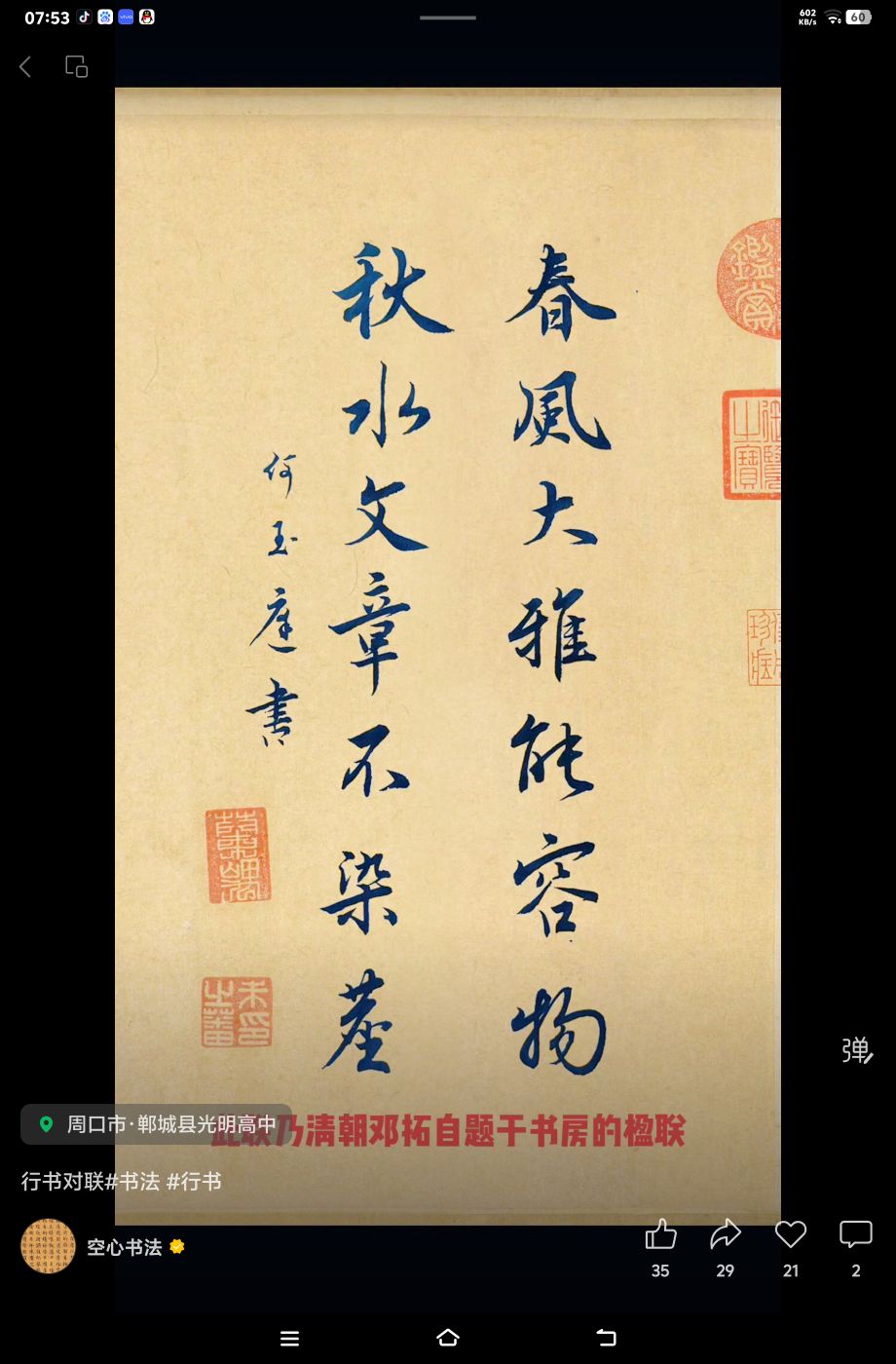
正當我望著漫天飛雪愁腸百結時,一個熟悉的身影,推著一輛老舊的三輪車,艱難地碾過積雪,出現在巷口。是校門口修車鋪的李爺爺!他裹著一件洗得發(fā)白的舊軍棉襖,帽子和肩頭都積了厚厚一層雪,像個移動的雪人。看到我趴在窗邊張望的焦急模樣,他咧開嘴,呵出一團白氣,笑容從皺紋里漾開:“丫頭,雪太大了,爺爺送你一程!”
我雀躍地鉆進三輪車后斗。李爺爺不知從哪兒變出一塊厚厚的棉墊鋪上,甚至從自己懷里掏出一個還有些溫乎的暖水袋,塞到我冰涼的手里。車子“嘎吱嘎吱”地啟程了。李爺爺佝僂著背,身體前傾,幾乎伏在車把上,每蹬一下踏板都需要使出全身的力氣。車輪在積雪中壓出兩道深深的轍痕,寒風卷著雪沫打在他的臉上、脖頸里,但他只是偶爾抬手抹一把,依舊穩(wěn)穩(wěn)地掌著方向。我捧著暖水袋,看著他那件舊棉襖后背上漸漸被汗水洇濕又凍成冰霜的痕跡,鼻子一陣發(fā)酸。
終于到了家門口。我跳下車,正要道謝,李爺爺卻從車筐里又摸出一個用舊棉衣裹得嚴嚴實實的東西。他一層層打開,一股混合著焦糖香氣的溫暖熱浪撲面而來——是一個胖乎乎的、烤得正好的紅薯!“知道你惦記著奶奶,路過攤子,就給你也捎了一個,快拿著,還熱乎呢。”他把紅薯塞到我手里,那溫度燙著我的手心,也瞬間燙熱了我的眼眶。
我還未來得及說出完整的謝謝,他已經笑著擺擺手,調轉車頭,那略顯笨拙的背影,很快便重新消失在茫茫風雪織就的簾幕之后。我站在門前,捧著那個滾燙的紅薯,望著他消失的方向,久久不動。那晚的雪光,映著千家萬戶的燈火,明明是一片清冷之色。但我卻覺得,李爺爺和他的三輪車,就像一道劃破嚴寒的暖光,不僅照亮了我回家的路,更在我年少的心田里,深深埋下了一顆名為“善意”的種子。原來,最動人的溫暖,未必是太陽般的熾熱耀眼,它也可以是雪夜里,一個陌生人默默遞來的、剛好暖手的溫度,純粹如雪,卻能抵御整個歲月的風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