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至吃餃子還是湯圓##創作挑戰賽十一期#
冬至有娘,便是暖年
王綿民

冬至的風,裹著清冽的涼意掠過窗欞,東方的天幕被初升的日頭染成一片暖紅。清晨五點多,我便從輾轉中醒來,昨夜近零點才合眼,發小武圣田的一條朋友圈,卻像一粒石子,在我心湖里漾開圈圈漣漪,攪得人再也無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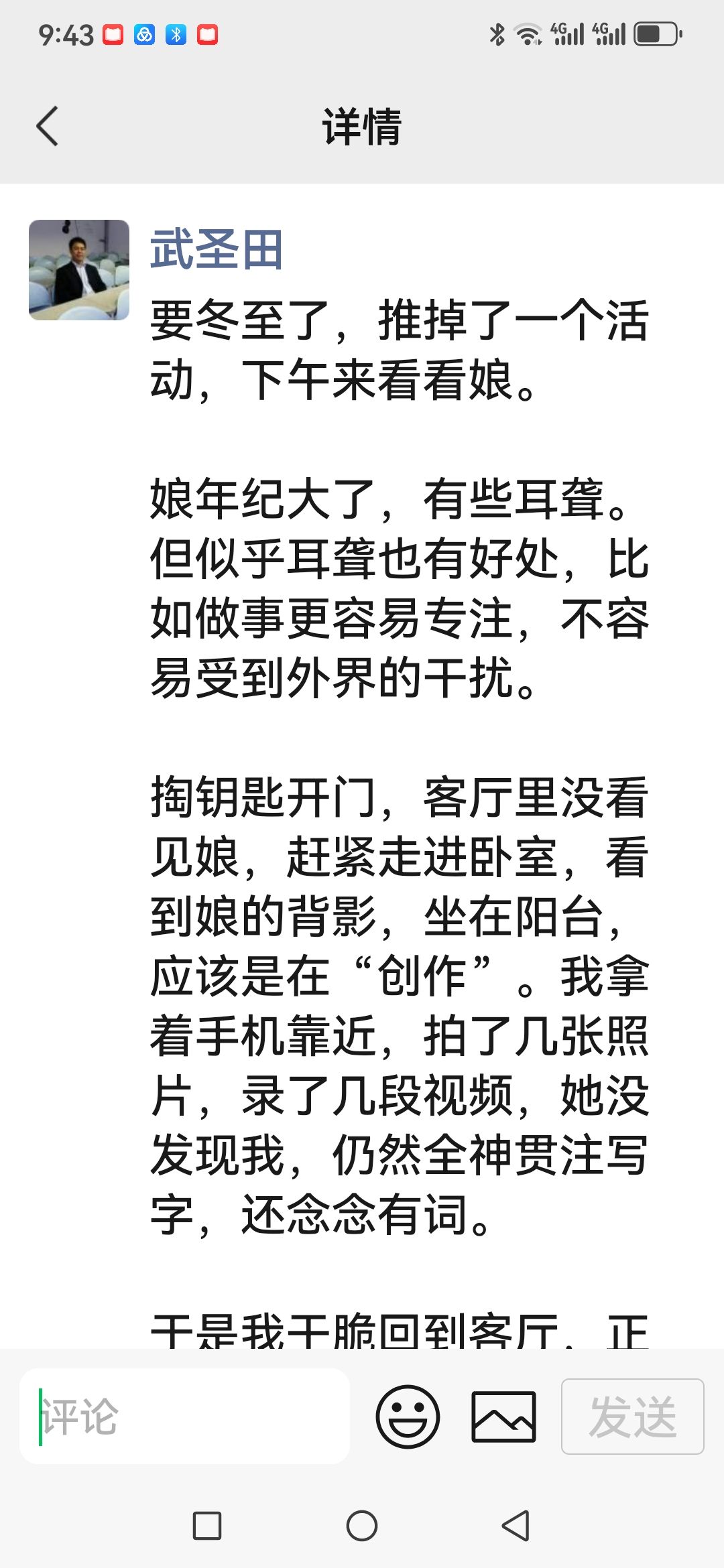
點開那條朋友圈時,我的眼眶倏然就濕了。武圣田推掉了推杯換盞的應酬,踏著冬日的清寒,去老屋看娘。那個耳朵有些聾的老人,正坐在陽臺的暖陽里,專注地寫寫畫畫。筆尖劃過紙張的沙沙聲里,她念念叨叨,把對兒女的牽掛、對過往親人的惦念,都揉進了一筆一劃的溫柔里。武圣田就那樣在娘的身后靜靜站了二十多分鐘,生怕驚擾了這份安然的專注。他輕手輕腳地往復于客廳與臥室之間,悄悄錄下一段段細碎的日常。臨走時,他的衣兜里揣著娘親手炸的麻葉,金黃酥脆,裹著滿當當的煙火氣。

這尋常到不能再尋常的一幕,竟是我如今最羨慕的奢望。
我的父親離開已有三十年,明年,便是母親離世的第二十周年。那些浸著煙火與汗水的舊時光,總在不經意間,就從記憶的深海里翻涌上來。80年代的日子,清貧得像一碗寡淡的稀粥。為了湊我的學費,身患嚴重皮膚病的父親,硬是挑起了一副沉甸甸的菜擔子。他不會騎自行車,就憑著一雙腳,一步一步丈量著鄉間的土路,走村串巷地叫賣。斑駁的皮膚被汗水浸得泛紅發癢,肩頭的擔子壓彎了他的脊背,卻壓不彎他供我讀書的執念。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那佝僂的背影,成了我記憶里最酸楚的風景。
母親的雙腳,早已被歲月與勞作磨得嚴重變形。她的日子,從沒有半分閑暇。白天,她要下地侍弄莊稼,泥土沾滿褲腳,汗水濕透衣衫;傍晚回家,灶膛的火苗還沒熄滅,她又要忙著生火做飯、喂豬養雞,把一大家子的瑣碎,打理得井井有條。夜里,昏黃的煤油燈搖曳著微光,母親戴著老花鏡,坐在燈影里,一針一線地縫補我們磨破的衣裳。變形的手指在針線間穿梭,每動一下,都藏著說不出的疼。
寒冬時節,母親的手總是皴裂得厲害,一道道裂口像干涸的河床。可我總忘不了,每當我的后背發癢時,只要母親把皴裂的手掌伸進我的衣服里,輕輕摩挲幾下,那癢意便瞬間消散。如今想來,那雙粗糙的手掌,比任何精致的癢癢撓都要解癢,那是歲月沉淀的溫度,是母親獨有的溫柔。
我還記得,年少時的我,一到冬天手腳便長滿凍瘡,嚴重時甚至潰爛流膿。這成了母親最大的心病。她熬夜為我縫制厚實的手帽,一針一線都縫進了牽掛;她四處打聽土方,熬制溫熱的湯藥,小心翼翼地幫我浸泡傷口。每當看到我凍得紅腫潰爛的雙手,母親的眼眶總會泛紅,心疼的淚水,悄悄滴落在我的手背上,溫熱而滾燙。
武圣田說,娘的耳聾,倒讓她做事更專注了。那一刻,我忽然就懂了。父母的世界從來都不大,小小的一方天地里,裝滿的從來都是子女的冷暖。就像武圣田的娘,沉浸在寫寫畫畫里,念叨著孩子們的柴米油鹽,追憶著逝去的故人,那份專注里,藏著最純粹的念想。而武圣田那份小心翼翼的守護,怕驚擾、怕打斷,悄悄記錄、靜靜陪伴,恰是成年子女對父母最溫柔的回饋。
可我,連這樣的機會都早已失去。
如今的我,只能在回憶里打撈那些細碎的溫暖:父親挑著菜擔子漸行漸遠的背影,母親燈下縫補衣裳時專注又疲憊的眼神,還有那皴裂手掌拂過后背的觸感,那盆溫熱的湯藥水,那頂厚實的手帽…… 那些曾以為理所當然的陪伴,那些被我忽略的日常,如今都成了遙不可及的念想。
我曾在文字里寫過許多關于親情的感悟,卻總也寫不盡 “子欲養而親不待” 的遺憾。這份遺憾,在這個冬至,在看到武圣田朋友圈的那一刻,變得愈發清晰刻骨。原來,親情從不是什么轟轟烈烈的壯舉,它是冬至里的一次探望,是身后默默地守望,是臨行時塞滿衣兜的麻葉,是煤油燈下縫補的衣裳,是皴裂手掌拂過的溫柔。
“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父母去,人生只剩歸途。” 這句話,在這個冬至的清晨,重重地叩擊著我的心門。
冬至已至,歲寒情深。愿武圣田的娘健康長壽,歲歲無憂;愿每一個尚有父母可依的人,都能珍惜當下的每一寸陪伴,把孝心藏進日常的點滴里。別等時光老去,別等親人遠去,才驚覺,那些平凡的相守,原是生命中最珍貴的寶藏。
這個冬至,風依舊微涼,可想起父母的模樣,心底便涌起一陣暖意。原來,只要父母的身影還在記憶里鮮活,歲歲年年,便都是暖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