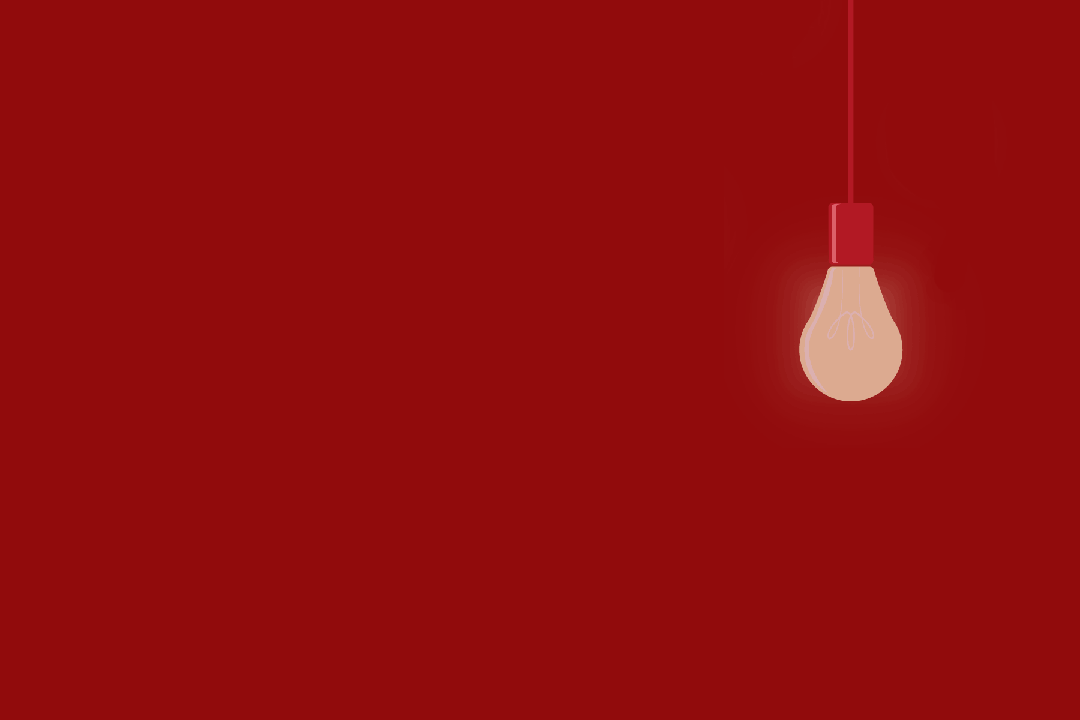華為禁令背后:一場關于“中國威脅”的英國議會敘事戰

Francisca Da Gama
格林威治大學商學院國際商務高級講師
Kim Bui
格林威治大學商學院國際商務高級講師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34, No.156, 2025
導讀
當科技競爭遇上政治敘事,華為在英國的經歷堪稱一部外交情景劇,而議會成了其中最戲劇化的舞臺之一。從“黃金時代”的科技伙伴,到英國口中的“安全威脅”,背后不是技術指標的較量,而是一場圍繞身份、安全與話語的復雜博弈。值得玩味的是,這些辯論中反復出現一種被稱為“政治漢學主義”的敘事濾鏡,即通過精心選擇事例、構建二元對立,將中國企業簡單刻畫為“中國威脅”的延伸。英國對華為政策的大轉彎,與其說是單純的安全考量,不如說是一場“話語建構”與“盟友壓力”共謀的結果。如今,從荷蘭光刻機出口管制到美國《芯片與科學法案》,從“清潔網絡”到科技聯盟重組,華為的劇本正在全球多地上演。技術問題被政治化、供應鏈被打上價值觀標簽,已然成為大國競爭的新常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路,正在被鋪上一層又一層看不見的“濾網”。而讀懂這套“濾網”的運作邏輯,或許才是突破圍堵的第一步。
從合作到禁令:英國對華為政策的轉變
與“五眼聯盟”部分盟友的激進立場不同,英國在華為問題上最初并未選擇直接禁止,而是采取了一種更為審慎的迂回策略,試圖以此來平衡英中經貿關系和英美“特殊關系”。得益于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推動,華為在時任工黨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執政期間進入英國市場。2005年,華為與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m)簽署寬帶網絡升級合同,這是華為在歐洲的首個重大合同,標志著其“走出去”在歐洲取得了重大突破。隨后的十年間,華為在英國的影響力持續深化。特別是在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時期,伴隨著兩國關系步入“黃金時代”,華為與英國的合作關系也不斷得到鞏固。至2019年9月,華為通過其創新研究項目資助,已與35所英國大學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
然而,特蕾莎·梅(Theresa May)出任首相后,此前英國對華為的的開放歡迎迅速為嚴苛地審查所取代。梅政府乃至整個保守黨內部,在如何對待中國和華為的問題上出現了深刻分歧,且隨著“脫歐”議題疊加而進一步加劇。2019年4月,英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曝出政府已同意華為有限度參與其非核心網絡建設,這一事件直接導致國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被解職,進一步加劇了黨內分裂。與此同時,美國的接連施壓,也將華為所謂的“安全問題”推至風口浪尖。
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接任首相后,盡管他本人一度展現出親華姿態,但其政府在對華為政策上明顯向美國立場靠攏。2020年1月,英國政府宣布將華為在英國5G市場的份額限制在35%,并禁止其參與核心網建設。然而,這一初步立場在數月后發生根本性逆轉。在2020年7月的議會辯論后,政府最終決定全面禁止英國電信運營商采購華為5G設備,并要求在2027年前拆除已安裝的設備。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華為是當時英國唯一擁有專屬安全風險緩解策略(bespoke mitigation strategy)的電信運營商。為評估其潛在運營風險,英國早在2010年就設立了“華為網絡安全評估中心監督委員會”。該委員會在2018年的評估結論是,華為參與英國5G網絡帶來的國家安全風險是“可管控的” (could be managed)。盡管后續報告提及了一些技術缺陷,但在2019年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NCSC)明確指出,并未發現這些缺陷是中國國家干預的結果。然而,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技術專家的專業意見最終讓位于政府的政治考量。隨著美國對華為供應鏈實施制裁,英國以無法再保證華為產品安全為由,最終將其正式列為“高風險供應商”。華為這個最初作為英中經濟關系深化的象征,在政治敘事中逐漸被等同于中國國家實體,并默認成為一種安全威脅。
分析框架:政治漢學主義視角下英國對華為的敘事策略
為評估英國圍繞華為的政治敘事,本文引入“漢學主義”作為一種批判性視角。該理論揭示了全球化時代下,西方認知與利益如何深刻影響其關于中國的知識生產,以此來揭示涉華敘事背后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根基。文章采取了顧明棟(Meng Dong Gu)關于漢學主義的定義,將漢學主義視為一個由對待中國的態度以及中國事物的生產方式而構成的一個知識處理系統,受控于以西方為中心的觀點、信仰、價值觀、認識論、方法論與判斷標準。麥克斯米利安·邁爾(Maximilian Mayer)提出的所謂“數字東方主義”(digital orientalism)也同樣存在著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偏見,片面地將中國技術力量的崛起視為一種威脅,而忽視其任何積極貢獻。
有學者通過分析圍繞對華貿易戰的論述,識別出將中國經濟行為“野蠻化”敘事的四個主題:貿易作弊者(trade cheat)、知識產權竊賊、黑客(網絡間諜)和“惡棍(villain)”。這類敘事通常將中國框定為“野蠻”方,其目的在于正當化西方自身采取的“野蠻”策略,以此為攻擊華為提供合法性。
事實上,此類敘事框架在英國亦有體現。為此,本文將審視英國議會辯論中關于華為的敘事轉變,以此來探究“政治漢學主義”如何塑造了針對華為的話語,即通過建構一套知識體系來推進特定的中國觀,從而服務于某種帶有西方偏見的政治敘事。既有研究普遍將地緣政治博弈視為解讀華為遭遇美西方圍堵的核心視角,本研究試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證地緣政治博弈與漢學主義敘事之間相互建構的共生關系。一方面,地緣政治博弈為漢學主義敘事提供了物質層面的競爭動力和現實注腳;另一方面,漢學主義敘事則為地緣政治博弈建構了話語層面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從而將具體的利益博弈升格為一場關乎價值與秩序的意識形態對抗。
研究方法與數據分析
作者對議會辯論進行了敘事分析,通過檢索英國議會議事錄在線數據庫中自2011年首次提及至2020年7月決定移除華為期間所有包含“華為”一詞的記錄,得出初始樣本102份,篩選出下議院26場辯論作為分析重點。最終分析樣本涵蓋24份辯論記錄,總計276923詞,來自107名議員的466個獨立“話語單元”。
作者將“話語單元”定義為議員就華為某一特定主題所發表的持續性評論,采用定性主題分析法識別主要共同主題,并對相關文本進行編碼,最終形成四個主題(技術創新者與合作者、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損害英國與盟友關系、西方對立價值觀的化身)。在此基礎上,作者還捕捉了每位議員話語的情感傾向,編碼為“積極”、“消極”或“中立”。
在全部編碼話語中,保守黨議員占69%,工黨議員占18%,其他黨派議員占13%。在2020年1月至7月決定禁止華為的關鍵辯論期間,發言的保守黨議員中,政府部長僅占16%,表明大部分發言來自保守黨后座議員。在整個研究時段內,73%的話語為消極,7%為積極,20%為中立。其中中立話語多由政府部長發表,職位的身份約束要求其在公開辯論中保持政策中立;在消極話語中,66%來自保守黨議員,20%來自工黨,14%來自其他黨派。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作者對所有議員的話語和情感進行了編碼,但下文討論主要聚焦推動關于華為辯論的保守黨議員,由于其在辯論中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并左右了輿論走向,因此本文研究重點也在于分析影響保守黨政府政策轉變的因素。
基于保守黨議員辯論文本的實證分析
(一)創新與合作:從“黃金時代”到“依賴枷鎖”
在英國議會關于華為的早期辯論(2012-2013年)中,核心主題是肯定其作為“創新者與合作者”的身份。卡梅倫曾回應保守黨議員史蒂夫·貝克(Steve Baker)的質詢,欣然歡迎華為投資,并強調英國的優勢在于訓練有素的工程師、優秀的大學和開放的商業環境。然而,自此之后,“創新與合作”的主題直至2019年才再次出現,且此次出現是為了質疑華為作為創新者的形象。雙方關系被負面地描述為一種“依賴”,華為對英國的貢獻受到質疑,甚至被污蔑為導致英國技術衰退。在相關辯論中,依賴華為被描述為阻礙西方技術發展,服務于中國產業政策,這種敘事甚至被類比為“毒品依賴”。
盡管存在質疑,認為華為是技術領導者的觀點在2020年3月的辯論中依然存在。前內閣大臣杰里米·懷特(Jeremy Wright)表示,在滿足安全要求的前提下,應選擇業界公認的性價比更優的設備。然而,議員伊恩·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則對華為的技術權威提出挑戰,認為其技術領先是“無稽宣傳”。
這些爭論反映了行業專家與政府批評者在華為政策上的深刻分歧。質疑華為作為創新者的角色實際上是質疑英國與華為的合作,兩類觀點表面上相互沖突,卻都維系著西方優越性的理念。即使在對華為表示支持的聲音中,也潛藏著漢學主義的邏輯,即合作的前提是英國必須保持其作為技術領導者和規則制定者的地位。
(二)國家安全:從風險可控到“引龍入室”
與質疑華為技術創新者身份緊密相關的是安全擔憂。有觀點認為,華為技術的質量問題使其更容易受到網絡攻擊。與此同時,隨著漢學主義敘事地演進,華為這一商業實體被抹黑為中國政府的“政治化身”,污稱華從事 “間諜活動”。2017年頒布的中國《國家情報法》引發了英國對“國家安全”的擔憂,盡管“五眼聯盟”國家自身也設有類似的法律,且華為公司和中國政府多次表示將嚴格遵守所在國的法律,但仍未能打消其顧慮。
與此同時,針對華為股權結構的質疑也不斷發酵,越來越多的議員批評其并非真正的私營公司,甚至將允許華為接入英國網絡被比作“把我們家的鑰匙交給竊賊”。然而,與此相對的是,NCSC負責人卻在2019年的專業評估聲明中指出,英國對華為的監管是“全球最嚴格、最嚴密的體系”。
此外,議會關于國家安全論述的權威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建立在廣泛的專家智識之上,而是反復援引少數幾位關鍵的政治人物,如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負責人邁克·伯吉斯(Mike Burgess)和前英國秘密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迪爾洛夫(Richard Dearlove)。迪爾洛夫的信譽尤其存疑,其曾在伊拉克戰爭調查中被指責夸大安全威脅。盡管存在專業領域的競爭性敘事與核心人物的可信度質疑,但基于伯吉斯和迪爾洛夫觀點的負面敘事仍在后期主導了議會的辯論議程,折射出政治敘事動力和客觀事實評估之間的內在張力。
(三)盟友關系:戰略自主與陣營壓力下的戰略兩難
在與華為保持合作關系的風險認知中,還潛藏著英國對維系與盟友關系的深層焦慮。伴隨著英國脫歐這一關鍵節點的來臨,保守黨內部路線分歧被進一步放大。梅政府曾試圖在華為議題上采取更加獨立且區別于美國的政治立場,強調英國擁有制定符合自身利益政策的權力。即使在2020年,仍有議員在議會辯論中強調,除非美國提出基于證據的合法安全理由,否則英國應當堅持自身的判斷。然而,由于英國脫歐后亟需重塑與傳統盟友的緊密關系,在此背景下,繼續與華為合作開始被視為可能阻礙這一戰略目標實現的不確定性因素。越來越多的議員警告稱,堅持與華為合作可能導致英國在關鍵盟友網絡中陷入孤立。
這些辯論不僅反映了后脫歐時代保守黨對華政策的戰略性轉變,也揭示了其黨內圍繞“全球英國”身份愿景的深刻內部分歧。如何在追求戰略自主與維系盟友關系之間取得平衡,成為后脫歐時代英國外交政策面臨的主要困境。一方面,“全球英國”的身份愿景要求其展現出獨立行動的能力,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并努力開拓非西方市場;另一方面,來自“五眼聯盟”的情報紐帶與英美“特殊關系”牢牢縛住了其手腳,使得其難以承受在核心安全議題上與美國決裂的代價。英國對華為的禁令,不是出于經得起技術檢驗的安全威脅,而是在這一結構性困境中做出的地緣政治選擇。此舉表明英國面對中美戰略競爭,維系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的優先級最終壓倒了其對戰略自主的訴求。
(四)價值觀敘事:規則秩序與文化符號的合流
在后脫歐時代的政治話語中,“五眼聯盟”所謂的民主價值觀被塑造成具有道德優越性的政治符號,這一敘事與國家安全關切及盟友協同立場相互借重,共同構成對華戰略競爭的意識形態基礎。這一時期的議會辯論明確將中國定位為“制度性對手”,指責其行為 “試圖挑戰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在此背景下,關于依賴華為的敘事也與所謂的民主價值觀聯系在一起,其私營企業屬性反復遭到質疑,甚至被惡意塑造為背離西方自由貿易精神的“不公平競爭者”。與此同時,人權問題也被刻意地嵌入對華政治修辭,在議會辯論中推向“武器化”,服務于孤立和遏制中國的特定政治目的。
價值觀敘事打破了傳統兩黨的政治分野,對華為的強硬立場罕見的凝聚起了跨黨派的“政治共識”。在此背景下“基于規則的秩序”成為高頻詞,有議員在演講中進一步提出所謂“文化代碼”(cultural code)的概念,詆毀華為的技術滲透將改寫英國社會的文化基因與個體自由的傳統邊界,將華為描繪成對英國文化主權的“威脅”。這套話語體系精準切中了“全球英國”尋求身份錨點的內在焦慮,其所援引的文化規范與規則秩序,本質上預設了西方價值的普世性與道德優越地位。
結語
對英國議會華為辯論的分析表明,其政策轉向既源于對中國科技崛起的擔憂,也迫于美國維系其霸權的外部壓力。漢學主義視角為理解英國涉華敘事的轉變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角,即這種敘事事先將中國框定為需要警惕的對象,從而刺激了針對中國的負面認知。
盡管顧明棟對漢學主義的概念化早于當代中國崛起,但隨著中國崛起,引發了西方的不安,漢學主義的影響反而日益深化。其揭示了西方如何通過自身視角建構關于中國的知識,以鞏固其意識形態偏見并邊緣化異見者。在議會的辯論中,英國不僅構建起針對華為的負面敘事,更試圖推廣一種更具偏見的對中國的認知。對英國議會辯論的漢學主義解讀進一步揭示了針對華為的負面敘事不是自然形成,而是通過精心選擇“證詞”、反復疊加特定文本建構起來的。這些敘事轉向不僅記錄了英國對華政策的戰略調整,更折射出其在對美“特殊關系”框架下難以擺脫的身份依附與利益捆綁。
譯者:季錦海,國政學人編譯員,外交學院國家安全學院。
來源:Francisca Da Gama, “ ‘Nesting Dragon, Soldier, Spy’: Shaping the Narrative on China Through Huawei in UK Parliamentary Debat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34, No.156, 2025, pp.1065-1080.
校對 | 張睿哲
審核 | 方桐
排版 | 崔梓玥
本文為公益分享,服務于科研教學,不代表本平臺觀點。如有疏漏,歡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