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之要,在于遠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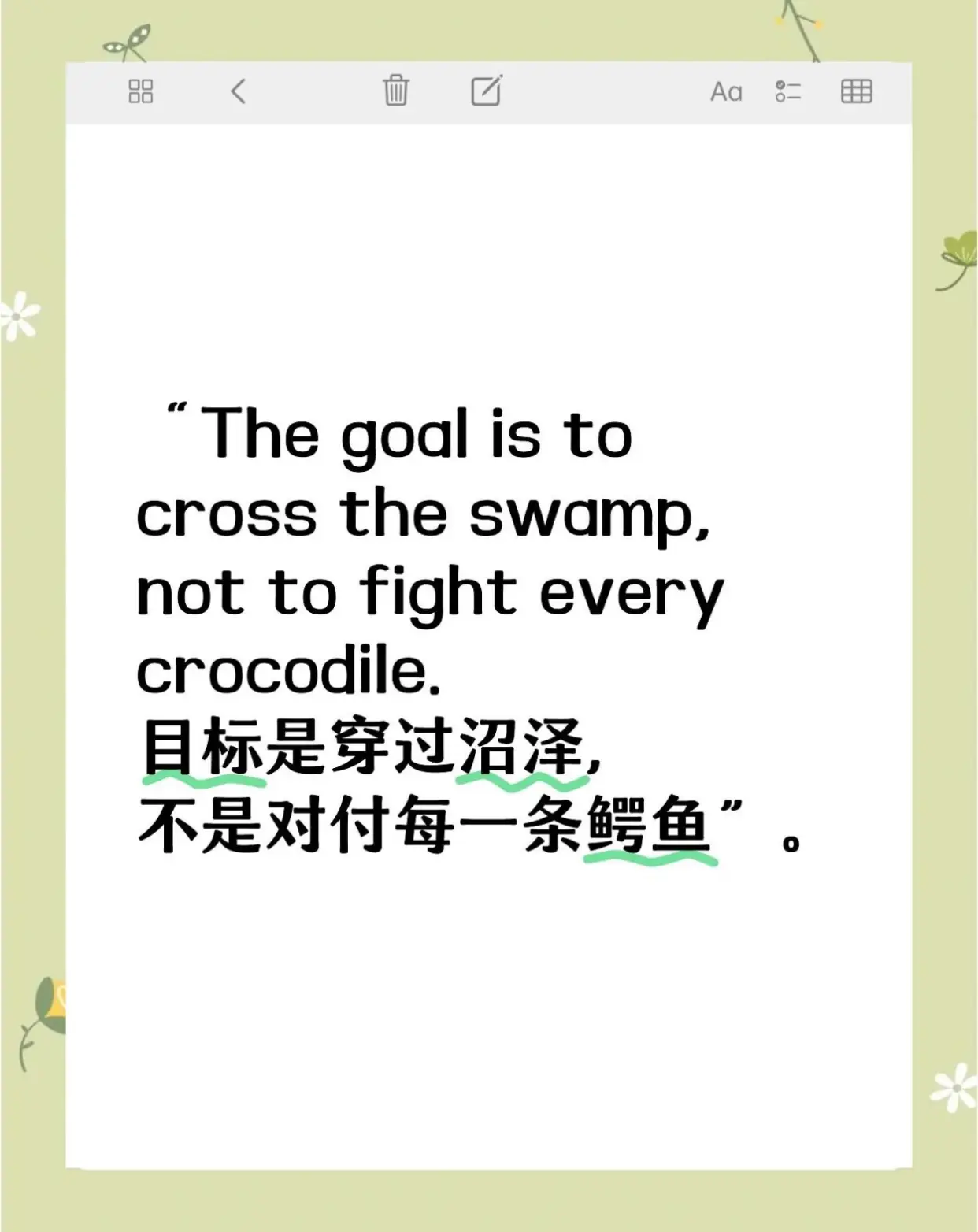
前行路上,常有泥淖橫生,鱷影隱現。有人怒而舉矛,誓與每一條浮出水面的惡獸纏斗,最終力竭于途,望不見彼岸?!度诵缘娜觞c》一語如晨鐘:“我們的目標是穿過沼澤,而不是對付每一條鱷魚。”此言洞穿迷障,揭示了生存與前行最樸素的智慧——將軍趕路,不追小兔。真正的行進者,不為路邊草葉掛懷,目光始終鎖住地平線上那真正要緊的目標。

世間太多苦役,源于將手段誤作目的,把泥潭中的倒影當作星空。 為一句口角輾轉反側,為蠅頭微利機關算盡,為無關褒貶耗盡心神……這些細碎糾葛,如沼澤中無數偽裝的鱷吻,一旦迎戰,便拖人墜入無休止的纏斗。它們消耗的不僅是時間與力氣,更是那份一往無前的清明心志。蘇東坡一生風雨,若他執意與每一道政敵的誹謗、每一次貶謫的屈辱貼身肉搏,又怎能吟出“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曠達?他看見了更遠的山水與更恒久的文章,故而能將足下泥濘,化作筆底煙云。心力有限,若盡付于應對瑣碎敵意,便再無余裕澆灌生命的主干。

然而,“不追小兔”絕非教人麻木不仁或逃避現實。它關乎一種更高明的戰略選擇:辨識何為真正值得交鋒的“鱷魚”,何為只需避開的泥沼水花。 這是一種深刻的專注力與定力。如航海者不會因每一道浪花而偏轉航向,他的羅盤永遠指向彼岸的燈塔。司馬遷忍宮刑之奇辱,非因懦弱,而是他深知,生命尚有未竟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壯業。他將個人榮辱的“小兔”輕輕拂開,將所有精神凝注于那部“藏之名山”的史家絕唱。這種專注,是一種主動的舍棄,是于紛繁世相中,為生命價值嚴格劃定邊界的勇氣。

行路的藝術,最終在于平衡“穿過”的智慧與“停留”的必要。 完全無視腳下,難免失足;只顧低頭搏殺,則永陷重圍。真正的行者,懂得在疾行中保持一份敏銳的感知,能辨清風向,避開真正的致命漩渦;同時,更懂得在必要時,為補給、為眺望、為調整步調而明智地暫停。但這種暫停,是為了更穩更快地前行,而非被路旁的野花或碎石羈絆了終身。

人生如行遠道,沼澤遍布。真正的勇毅,有時不在于斬殺了幾條鱷魚,而在于穿越沼澤后,衣襟雖沾泥濘,眼神卻愈發清澈堅定,始終記得——我為何出發,又要去向何方。那份不為沿途紛擾所動的專注,才是支撐我們走到最后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