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常由鮮血、生命寫成。
在明朝初年那段血腥的權力更迭中,方孝孺的名字以一種最為慘烈的方式被刻入歷史。當朱棣的軍隊攻入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這位被譽為“天下讀書種子”的大儒,面臨著一個簡單的選擇:為新皇帝起草即位詔書,或者,拒絕。

他選擇了拒絕,并且是以最激烈、最決絕的方式拒絕。于是,中國歷史上最駭人聽聞的刑罰之一——“誅十族”發生了。八百七十三人被公開處死,更有數千人被流放、充軍。方孝孺本人被凌遲處死,時年四十六歲。
四百多年來,對方孝孺的批評從未停止。明代思想家李贄直言:“人亦何必多讀書哉”,認為方孝孺的儒家信仰已異化為一種失去自我的盲目。民國歷史小說家蔡東藩更斥其為“迂儒”,質疑他為何非要激怒朱棣,招致如此慘烈的后果。
批評者的核心質疑在于:為了一場皇家內部的權力斗爭,值得賠上自己十族人的性命嗎?這究竟是“殉道”,還是一場以他人生命為籌碼的道德賭博?
從實用主義角度看,方孝孺的抗爭確實“無用”。他沒有改變朱棣登基的事實,沒有挽救建文帝的皇位,甚至沒能阻止“靖難之役”的發生。他的死,除了在史書上留下一個慘烈的符號,似乎沒有改變任何現實。

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被牽連的族人、門生、朋友。他們中的大多數,與這場皇權之爭毫無關系,卻因為與方孝孺的關系而被“瓜蔓抄”式地牽連。方孝孺在廷上怒斥朱棣“燕賊篡位”,寫下“燕賊篡位”四字時,是否想到了這些人的命運?
然而換個角度,方孝孺的形象又完全不同。胡適曾將方孝孺視為中國歷史上“殺身殉道”的典范。在胡適看來,方孝孺所堅守的,并非僅僅是建文帝這個具體的人,而是一整套價值體系:王道、正統、仁義、氣節。
在方孝孺的世界觀中,朱棣的“篡位”不僅僅是一次政治權力的非法轉移,更是對整個儒家倫理秩序的顛覆。如果“以下犯上”可以被接受,如果武力可以決定皇位的歸屬,那么整個大明王朝的合法性基礎將被動搖,社會的道德秩序將徹底崩潰。
從這個意義上說,方孝孺的抵抗,是在用生命捍衛他認為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他并非不怕死,也并非不珍惜親人的生命,但當“道”與生命必須做出選擇時,他選擇了“道”。
方孝孺的真正困境,在于個人道德選擇與社會責任的沖突。
作為儒者,他追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最高道德境界。但作為家族領袖、師長、朋友,他是否有權讓成百上千的他人為自己的道德選擇付出生命的代價?
這種困境在儒家倫理內部其實早有張力。《孟子》既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但也強調“君子不立于危墻之下”。儒家既推崇氣節,也重視智慧與變通。
方孝孺選擇了氣節的極端形式。在朱棣已經掌握絕對權力的情況下,他的激烈反抗幾乎注定會引發最殘酷的報復。史載,朱棣最初并未打算誅殺方孝孺全族,是在方孝孺一再激烈對抗、公開辱罵后,才怒火中燒,下達了“誅十族”的命令。
這里有一個微妙的問題:方孝孺是否在潛意識中,期待著一個最為慘烈的結局,以成就自己“千古第一忠臣”的名聲?就像古代的刺客專諸、要離,似乎身邊人死得越多,就越能襯托其行為的“悲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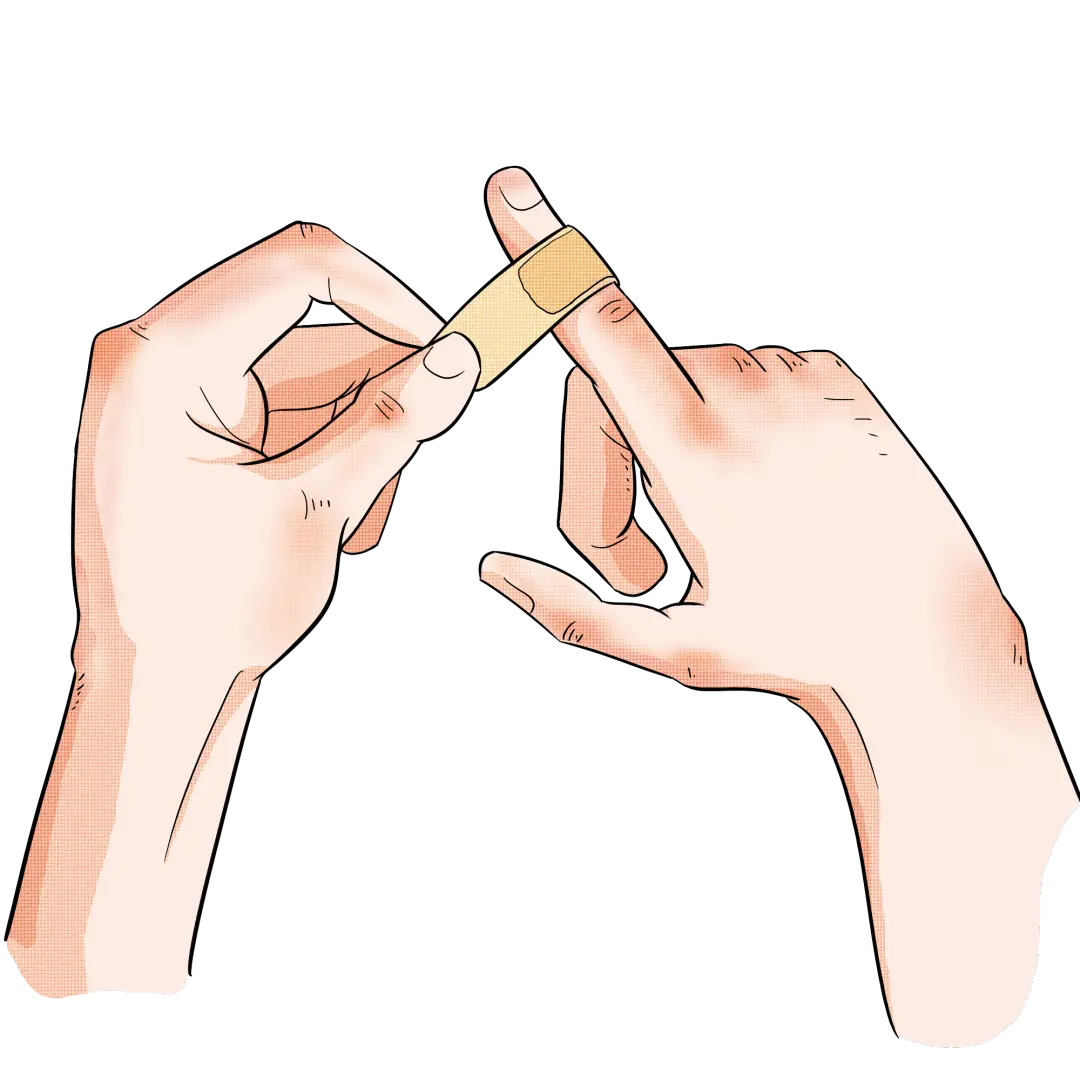
要理解方孝孺,必須回到明初的歷史語境。
明朝開國不足四十年,朱元璋以嚴刑峻法治國,士大夫氣節尚未在明初政治中完全建立。方孝孺的師承可追溯至宋濂,而宋濂一脈承襲的正是南宋以來浙東學派強調氣節的傳統。
在朱棣看來,方孝孺的拒絕不僅僅是對他個人的不服從,更是對其皇位合法性的根本否定。而在方孝孺看來,為“篡位者”起草詔書,意味著對自己畢生信仰的徹底背叛。
雙方都沒有退路。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不應陷入非此即彼的簡單二元。方孝孺既不是單純的“愚忠之臣”,也不是純粹的“殉道圣人”。他是一個在極端情境下,做出極端選擇的復雜人物。他的悲劇,既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也是專制皇權下士大夫困境的集中體現。
今天,我們在評價方孝孺時,往往帶著現代的個人權利觀念,難以理解那種將“道”置于生命之上的價值排序。但我們也不能完全以現代價值觀去苛責古人,因為在方孝孺的世界里,某些原則確實比生命更重。
值得思考的是,方孝孺死后,民間對他的同情與敬仰并未隨時間消退。各地多有“方孝孺后裔”的傳說流傳,這或許反映了普通百姓對反抗強權者的一種樸素敬意——無論其反抗的具體原因是什么,那種不屈服于暴力的精神本身,就值得尊重。
方孝孺的故事提醒我們:歷史評價往往充滿張力,一個人的“氣節”可能是另一個人的“固執”,一個人的“殉道”可能是另一個人的“賭命”。在絕對的價值沖突中,沒有簡單的對錯,只有不同的選擇,以及這些選擇所付出的不同代價。
方孝孺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提出了一個永恒的問題:當原則與現實沖突,當信仰與生命對立,一個人應該何去何從?這個問題,四百多年后的我們,仍然在尋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