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以后,大唐在皇帝三次奔逃、國祚幾度傾頹的情況下,仍能如百足之蟲那樣死而不僵。關于唐朝最后一個多世紀的國運,近年來史學界多從藩鎮和朝廷的關系入手進行闡釋。
日本學者新見媛跳出唐朝看唐朝,在專著《唐朝的滅亡與歐亞東部》中,從藩鎮對外關系的角度切入,評析唐朝最終滅亡的原因,給讀者觀察這段歷史以全新的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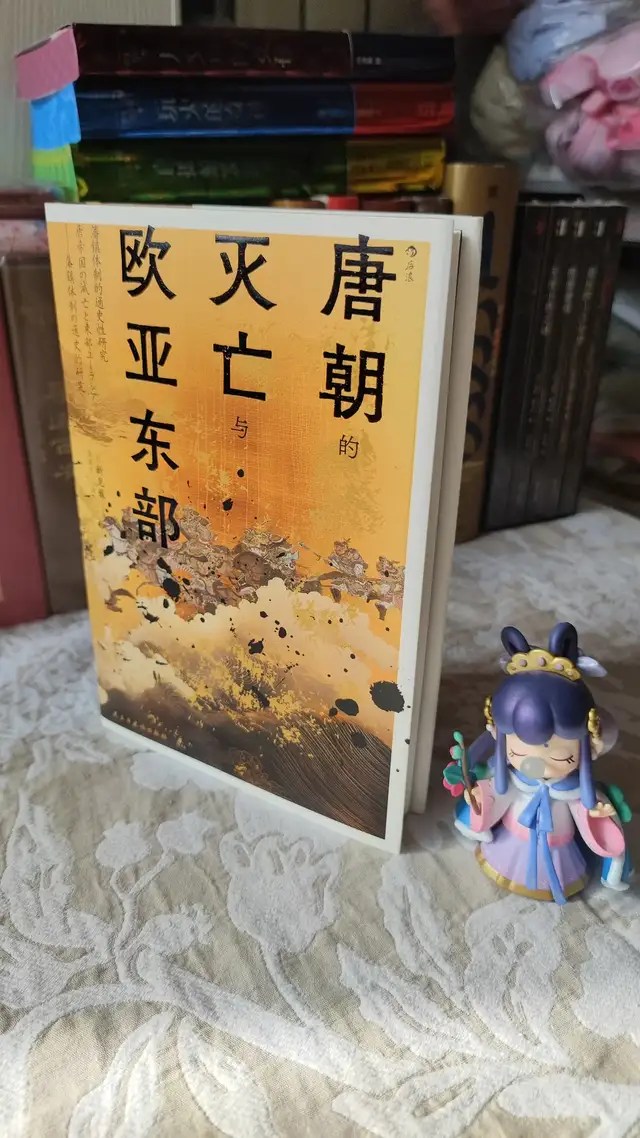

藩鎮,其名取自“藩屏王室”之意,原為戍邊防御而設。作者觀察的角度,實際上回歸了其設立的根本原因。一直以來,我們評價藩鎮,往往認為這些封疆大吏割據一方,依靠手中的財權和軍權與朝廷討價還價。本書則從藩鎮自身出發,對這些“土皇帝”所面臨的外部環境進行分析。
雖然藩鎮堪稱“帝國之癌”,但又像癌細胞需要依托母體存活那樣,對朝廷保持名義上的尊崇。為了攫取和朝廷談判的砝碼,藩鎮之間還需要通過類似合縱連橫的手段,通過聯姻、結盟等方式多方牽制,以達到微妙的平衡。這簡直就是春秋時期的翻版——諸侯雖然名義上承認周王,但暗地里都做著稱霸的美夢。
處于周邊的游牧民族勢力,在唐初短暫被“打服”之后,先后于唐代中后期恢復元氣。安史之亂以后,他們先是將目標對準大唐王朝,但很快發現很難消化這樣體量的對手,便將目標對準處于邊境地區的藩鎮。于是,藩鎮需要在朝廷、番邦和其他藩鎮的夾縫中謀求一席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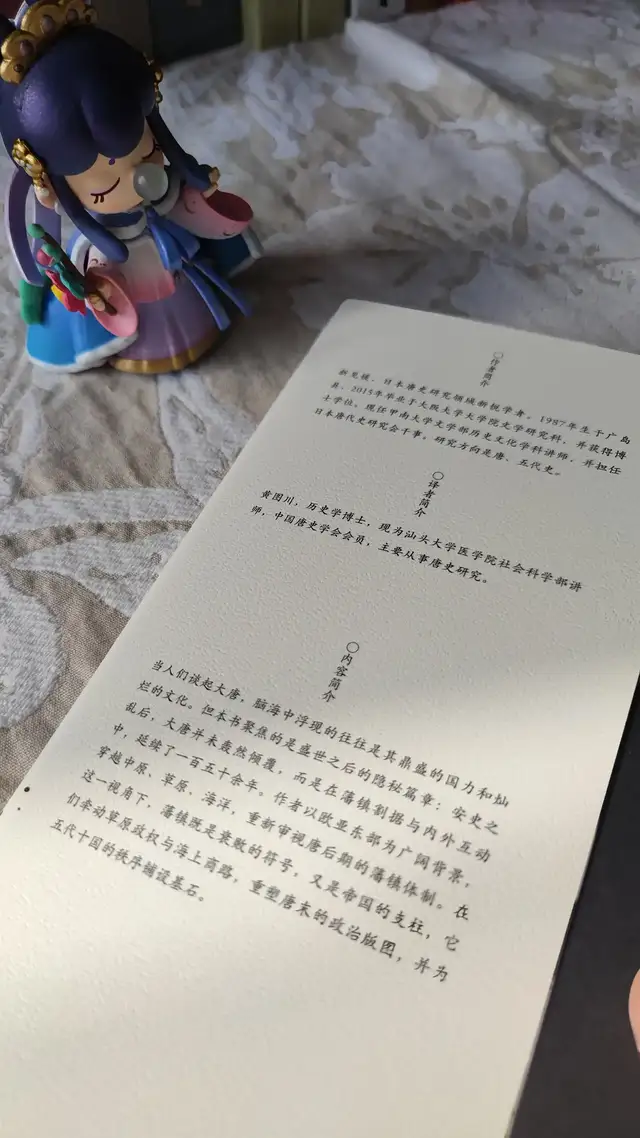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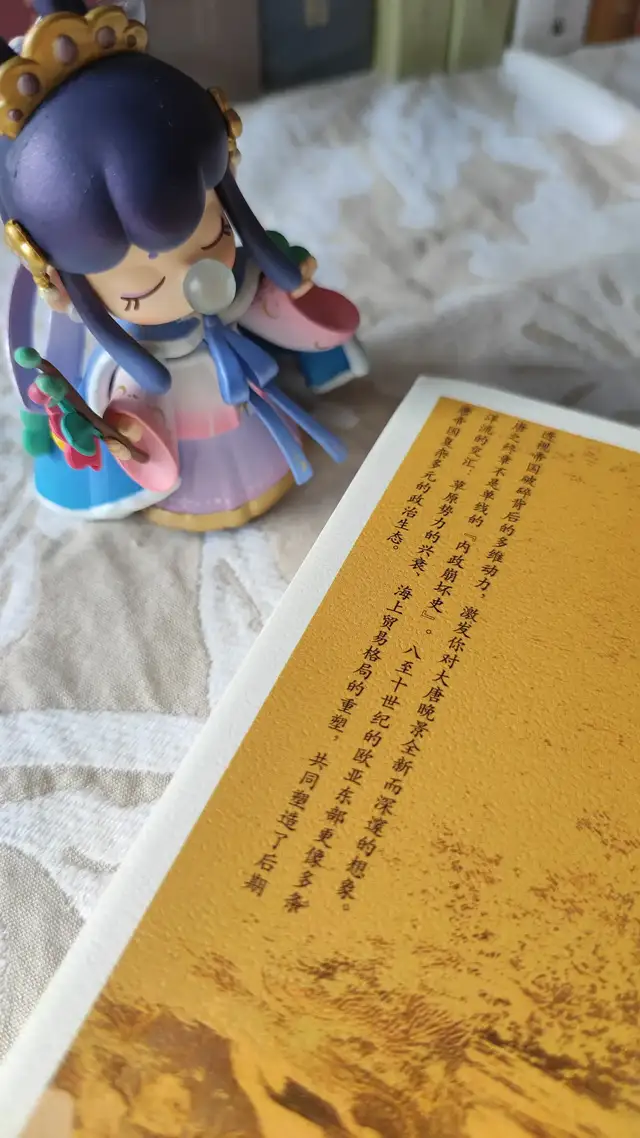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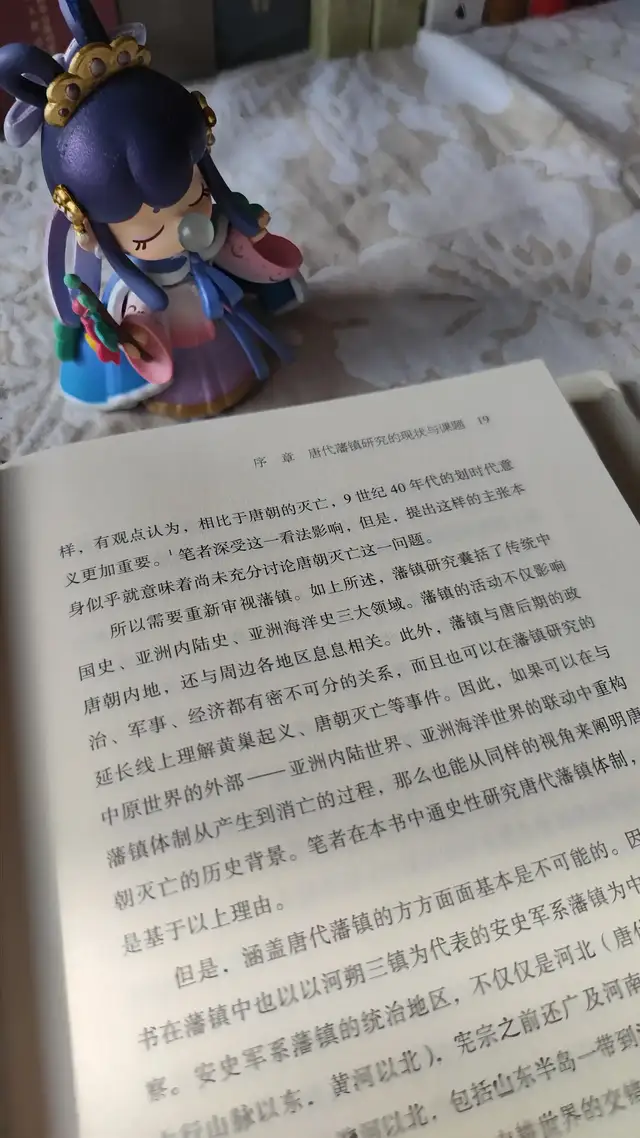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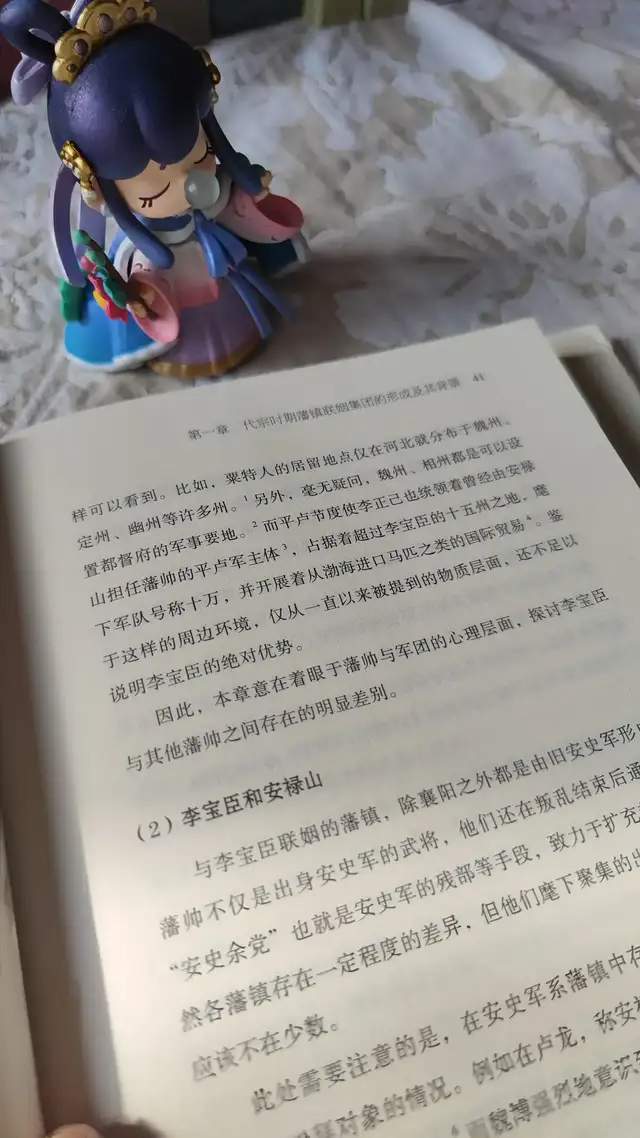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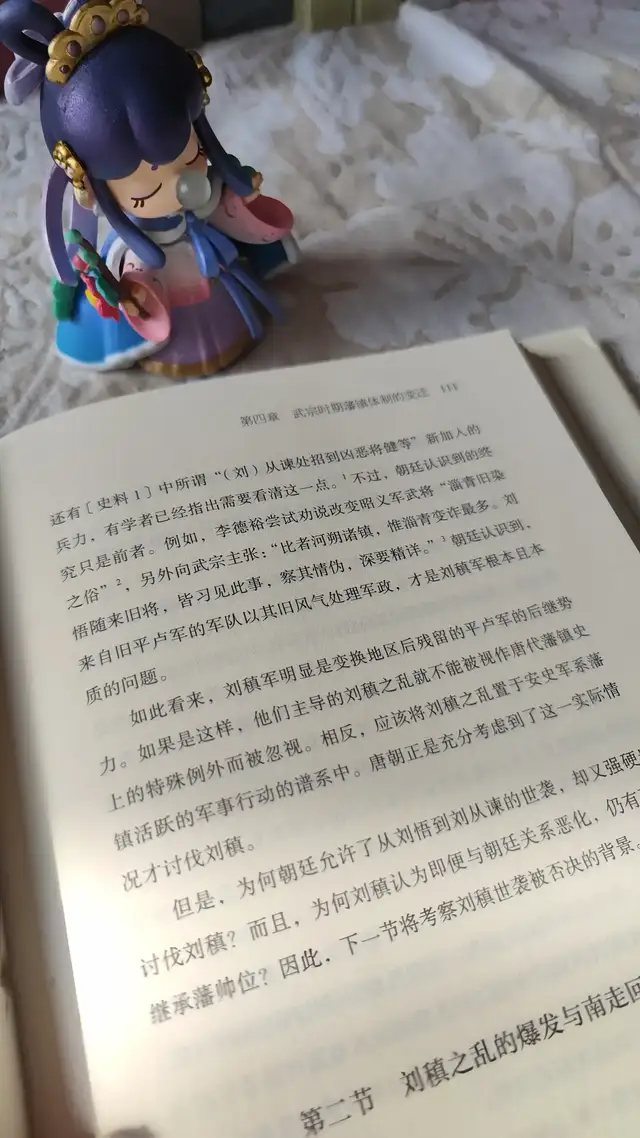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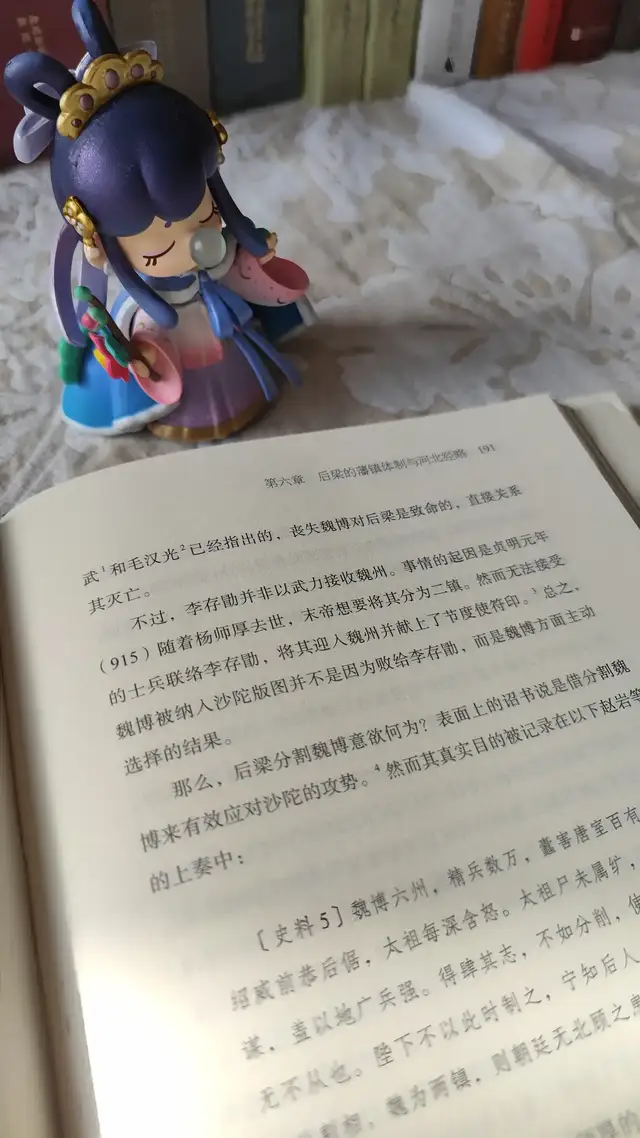
像藩鎮這樣受夾板氣的情況,春秋時期的秦、趙、燕等國也曾遇到過。但彼時,游牧民族直到秦朝統一中國才孵化出匈奴這樣強大的對手,而藩鎮此時面對的,從東北到西南,擺滿了新羅、契丹、沙陀、回鶻、吐蕃這樣的實力派。
順著這樣的思路,我們可以總結出唐代滅亡的原因:外部壓力越來越大,超出了藩鎮的承受能力,最終造成了唐王朝內部的全面崩潰。論及這一原因的前提,在于我們認為藩鎮在承壓時始終和朝廷是綁在一根線上的螞蚱,或者說在承壓初期依然矛頭對外。
這樣來看,我們既可以解釋黃巢和李克用相繼造反之后,緣何輪到朱溫摘了桃子,又可以解釋李存勖雖是沙陀出身,為何依然要扯著唐朝的虎皮來做大旗。
作者最后的結論不算十分切題,但不影響她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開闊的觀察視角。“中原中心論”近年來雖然已為史學界所匡正,但在普通人的印象里已經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積弊。當下已有相當一部分國內外學者將內亞史納入中國歷史的范疇進行考量,本書作者不過是將其中的觀點運用于評點中原王朝的得失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