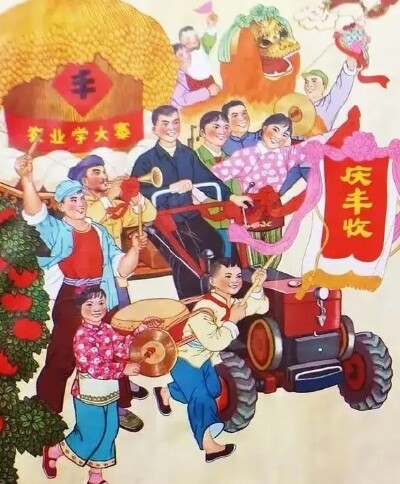一晃三十多年,我總忘不了小時候冬天,在寒冷的冬天取暖的日子。
秋末的時候,家家戶戶都會在村頭空地打煤球。
看著煤粉摻上黃土攪成黏糊糊的煤泥,再瞅著我爹攥著那個鐵模具,往煤泥里一扎一提,像打針似的一推把手,圓滾滾的煤球就“噗”地落了地。我蹲在旁邊,數著地上越擺越多的煤球,盼著它們快點曬干,好讓家里的爐子燒起來。
到了冬天,家里的蜂窩煤爐總是溫吞吞的,我就搬個小板凳,挨著爐子寫作業,手伸到爐邊,才勉強不凍手。蜂窩煤爐的火總是溫吞吞的,也就爐子周圍那一小塊地方暖和。條件好點的人家會盤個大鐵爐,燒整塊的原煤,添上幾塊,火苗“呼呼”往上躥,不一會兒屋里就熱得能脫棉襖。
可不管啥爐子,都得裝煙囪——那時候的冬天,總有人圖省事沒裝煙囪,或是煙囪堵了沒及時通,被煤氣悄無聲息地奪走性命,這是刻在村里人記憶里的后怕。
不下雪的晴天,白天要是家里沒人,為了省煤各家的爐子的風門就關得死死的,人們跑到村里背風的墻根曬太陽。
很多時候,村里某一家門口總會攏起一堆火,玉米桿、煙葉桿燒得“噼啪”響。再把紅薯埋進火堆的炭灰里,一會兒,紅薯就熟了,一陣香味能飄半個村。
圍著烤火的人們把手伸到火邊烤得發燙,后背卻還在冷風里凍得發麻,野地里烤火,就是這樣,半邊身子熱半邊身子涼。人們并不在意,還是扯著東家長西家短的閑話,換半邊身子再烤。
最難忘的還是在教室里烤火。講臺邊那個銹鐵爐,火苗弱得像打盹,離遠了一點暖意都沒有。下課鈴一響,我就跟著大伙往爐邊沖,可那些高個子男生力氣大,總能擠到最前頭,我根本沾不上邊。
沒辦法,就跟著女生們擠到墻根玩“擠油油”,一排人貼在墻上,兩邊使勁往中間拱,被擠出去了就揉著發麻的腰,跑到隊尾接著擠,擠得渾身冒汗,倒也忘了冷。
遇上晴天,我們就去教室的東山墻根曬太陽,靠在墻根瞇著眼,陽光曬得后背暖融融的,比烤火還舒服。
放學回家,我第一件事就是往爐子邊湊,把凍得僵硬的腳往爐沿上一放,鞋底的麻繩就“滋滋”冒白煙,媽媽做的千層底轉眼就烤出個黑窟窿。
那時候的冬天,手腳生凍瘡是常事,天冷凍得鉆心疼,開春一暖和,又癢得人直跺腳。
那些圍著爐火烤手、擠在墻根曬太陽的日子,雖然清寒,卻成了再也回不去的舊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