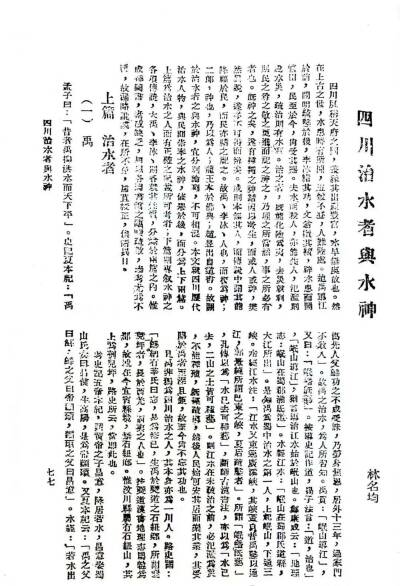溫造(約卒于835年),作為中唐時期兼具文韜武略的名臣,其生平事跡在《舊唐書》《新唐書》中均有專傳記載。他的仕途跌宕起伏,唐憲宗元和十三年(818年)因朝局變動被貶為開州司馬,時隔數年,于唐文宗大和年間(約827—835年)擢升為開州刺史。正是在這片當時被視作“地瘠民貧”的巴蜀邊地,溫造以卓越的治政才能深耕民生,尤其傾力擘畫水利建設,留下了一段澤被后世千年的治績佳話。
一、開州治政核心:濮巖水利的復興與修建
溫造治理開州的核心政績,集中彰顯于水利工程的興修。《新唐書·溫造傳》載:“徙開州刺史。開州地瘠民貧,造為筑陂塘,溉田千頃,民獲其利。”短短二十余字,精準勾勒出他以水利紓解民生困境的施政圖景。在農耕文明時代,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對于山地居多的開州而言,更是破解“地瘠民貧”的關鍵。溫造履任后,敏銳洞悉這一核心癥結,隨即主持修筑陂塘(兼具蓄水與灌溉功能的水利設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工程,便是后世銘記的“溫公陂”與“濮巖渠”。
關于這項工程的具體形制與區位,北宋《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三十八》留存了關鍵細節:“濮巖,在州北五里。有懸崖,瀑布高百余尺。唐刺史溫造鑿石渠,引水溉田。”這段記載不僅明確了工程坐落于州北五里的濮巖之地,更揭示了其巧借自然地勢的技術智慧——依托百余尺高的天然瀑布,開鑿石渠引流灌田。這種因勢利導的營造思路,既降低了工程難度,又提升了灌溉效能,充分彰顯了唐代水利工程的技術水準。后世清代及民國年間編纂的《開縣志》等文獻,均沿襲此說并進一步佐證其地理位置與歷史延續性,證實該工程直至明清時期仍有遺跡留存,足見其構筑之堅固與影響之深遠。百姓以其姓氏將陂塘尊稱為“溫公陂”,正是對其治水功績最質樸也最真摯的感念。唯因年代久遠,如今已無法考證其具體遺跡方位。
二、水利工程的多元價值:從農業賦能到區域安靖
溫造興修水利的直接初衷,便是破解開州“地瘠民貧”的困局。通過陂塘修筑與渠系貫通,上千頃旱地、薄田得到有效灌溉,農業生產條件實現根本性改善,糧食產量大幅提升,百姓生活隨之趨于安定。這一水利工程絕非單純的農業設施,更是兼具民生保障與扶貧紓困雙重屬性的治政舉措。
不僅如此,開州地處巴蜀邊地,多民族雜居,社會安定本就關乎區域穩固。溫造履任后,在興修水利的同時推行寬緩之政,減輕百姓賦役負擔。而水利建設帶來的農業豐收與民生改善,從根源上緩和了區域社會矛盾,為地方安定筑牢了根基。《舊唐書》記載其治下“為政清嚴,盜賊屏息”,這一治績的達成,與他以水利興生產、從源頭破解民生難題的施政方略密不可分。在此過程中,水利工程的價值已超越農業灌溉本身,成為維系一方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石。
三、歷史銘記:跨越千年的治績遺澤
溫造在開州的治績,既載入正史典籍,更深深鐫刻于地方歷史記憶之中。《冊府元龜·牧守部》評價其“在開州,以惠愛為政,民為立祠”,明確記載當地百姓為感念其恩德,專門立祠祭祀,這份自發的紀念,成為其治績深入人心的直接佐證。明清時期的《蜀中廣記·開州志》《開縣志》等方志文獻,均延續了對其治水事跡的記載,且提及“溫公祠”遺址的相關信息。這種跨越數朝的持續記述,正是溫造“千年遺澤”的有力見證。
一位地方官員的姓名,能與一項水利工程永久綁定,并在地方史志中流傳千年,本身就是對其治績的最高肯定。那條流淌千年的“濮巖渠”,不僅是滋養開州土地的生命之水,更成為流淌于地方史冊中的文化記憶,承載著百姓對賢吏的感念與對善政的向往。
四、開州治水:溫造水利實踐的奠基與升華
縱觀溫造的仕途生涯,其才能堪稱全面多元。晚年時期,他曾以儒臣之身“單騎定亂”,成功平定幽州兵變,彰顯出非凡的膽識與政治智慧;出任河陽節度使期間,他主持修復古秦渠枋口堰,“溉田五千頃”,治水成效更為卓著,被時人比作戰國時期的水利專家鄭國;最終官至禮部尚書,卒后獲贈右仆射,躋身朝廷重臣之列。
在這一系列治績中,開州時期的治水經歷具有特殊的奠基意義。這很可能是他首次獨立主持一方政務,并大規模開展水利建設的實踐,堪稱其“水利專家”聲名的起點。在開州治水過程中積累的勘察選址、因勢利導、工程組織等經驗,無疑為其日后在河陽開展更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堅實基礎。因此,開州不僅是溫造水利實踐的重要發端之地,更是其“以水利惠民生”施政理念走向成熟的關鍵階段。
溫造在開州的任職時光不過數年,但其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卻澤被后世千年,其“為政清嚴”“惠愛百姓”的施政理念,更成為流傳至今的精神財富。一條濮巖渠,一座溫公陂,承載的是一位唐代刺史務實為民的擔當與智慧。歷經千年風雨洗禮,其遺澤至今仍沉淀在開州的歷史肌理中,向后人昭示著何為“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為政初心與擔當。
(劉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