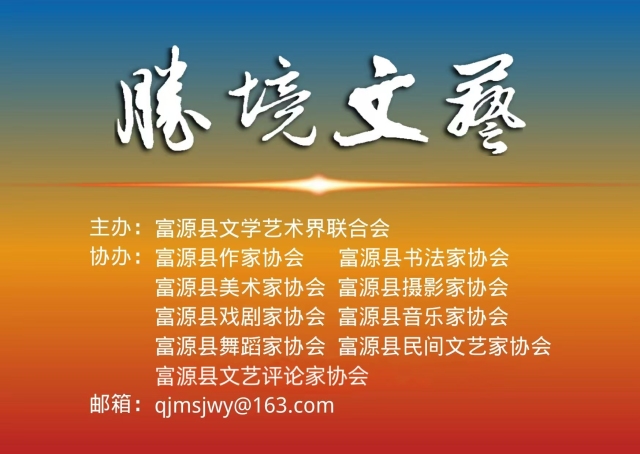云南作家陳景晟的小小說《帽子》,是一篇滿含故土氣息、浸潤著深厚情誼的佳作。小說以八十八歲的父親在與“我”的同學理正下棋時猝然離世為切入點,細膩鋪陳理正與“我”以及“我”父母幾十年來的情感交織與悲歡離合,讓讀者透過字里行間,真切感受那份超越血緣的真摯情義。
遺憾是這篇小小說的情感底色。父親與理正對弈時突然離世,作品并未交代具體死因,給讀者留下了想象空間;理正為父親的喪事忙前忙后,遠在夏威夷的“我”卻沒能見上父親最后一面;理正為父親取老花鏡,從窗臺墜落身亡,用生命為這份守護畫上了句號,這些細節都展現了理正與父親非比尋常的情誼;而“我”珍藏多年的粉色毛線帽,終究沒能送到理正墓前。這些遺憾像層層落雪,覆蓋在故事里,讓讀者深刻體會到現實的沉重——我們總在追逐遠方,卻常常忽略身邊那些默默為我們撐起一片天的人。
但理正的存在,為這份遺憾注入了溫暖的底色。學生時代,每次晚自習結束,他都會送“我”到樓下;畢業時,他送了“我”一頂粉色毛線帽,笑著說:“你戴在頭上就不會忘了我。”而在“我”遠走他鄉后,他更是主動扛起了照料“我”父母的責任,柴米油鹽、日常起居,大小事都一手張羅。父親去世后,他守在靈棚里,搶過父親的狗皮帽子說:“就當我給老爺子戴孝帽子了。”
理正的情義從不是轟轟烈烈的誓言,而是細水長流的行動。他從未要求過回報,甚至在“我”問起他的生活時,也只是淡淡一句“不說了,老爺子聽到了鬧心”,把所有委屈與孤獨都藏在心底。他不是“我”的親人,卻比親人更懂陪伴的意義;他不是父親的兒子,卻用半生時光,填補了“我”缺席的孝心。
母親在《帽子》中的戲份不多,卻起到了推動情節、承載情感的關鍵作用。母親把“我”出國后理正對他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盤托出,言語間滿是感恩。見理正戴的帽子太薄,母親便催“我”去家里取一頂暖和的給他。“我”匆忙中拿了父親戴過的狗皮帽子,母親見狀連忙阻止:“這是你爸的帽子,哪能讓理正戴他的帽子!”樸實的話語里,全是對理正的呵護。后來,母親提出要讓父親戴上老花鏡上路,體現了父母相濡以沫的深厚感情。而沉浸在喪夫之痛中的母親找不到家里的鑰匙,也為理正冒險爬墻取眼鏡、最終從窗臺墜落埋下了伏筆。
在《帽子》里,理正與“我”除了是同學關系,更是彼此情感共鳴的伙伴與成長的見證者。“我”問理正,老爸生前是不是對我不放心?理正回答“我”:“可不是,他說你離婚了,連個孩子也沒有,一個人住在國外,將來可咋整?”這段看似家常的對話里藏著不少信息:“我”與理正都是單身,并且彼此都在默默關注著對方。這不禁讓人聯想,如果理正沒有意外墜亡,故事或許會有另一種結局。作者巧妙設置這樣的悲劇性情節,可謂獨具匠心:一方面,用這種沉重的結局凸顯理正與父親“不是父子勝似父子”的深厚情感;另一方面,也為結尾的動人場景埋下了伏筆,讓作品的主題得到進一步升華。
父親去世前,正舉著“炮”準備攻打理正的“帥”,這場未完成的棋局,成了兩人情誼最鮮活的印記。“我”用黑色大理石在兩座墓碑之間砌了一個象棋盤,擺上一副象棋,這是對這份情義最真誠的致敬。對父親來說,這盤棋是他晚年孤獨生活里最溫暖的慰藉,是對理正“半個兒子”般陪伴的無聲認可;對理正來說,這盤棋是他“不求回報”守護的回響,讓他與父親能在另一個世界繼續“對弈”;對“我”來說,這盤棋是愧疚與感恩的補償——彌補了“我”缺席的陪伴,回應了理正的付出。
《帽子》里沒有驚天動地的英雄,只有普通百姓的悲歡離合,卻能讓讀者久久不能平靜。真正的情義,從來不需要血緣的綁定,它可以是一頂粉色毛線帽的約定,一盤未下完的象棋,一座連接生死的墓碑;可以像理正那樣,用一生的沉默與行動守護他人,成為寒風中最溫暖的光。這份超越血緣的情義,比冬日的落雪更厚重,比夏威夷的陽光更熾熱,散發著令人回味無窮的獨特魅力。
(刊《曲靖日報》)
來源:掌上曲靖
編輯:詹宇涵
審核:盧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