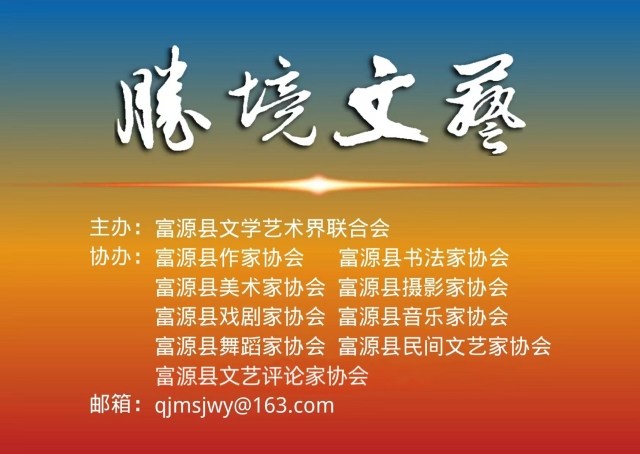父親在東北最冷的三九天去世,享年八十八歲。
去世前,父親正在和理正下象棋,當父親舉起一枚“炮”準備打向對方的“帥”時,胳膊卻突然僵住了。
理正是我的同學,后來我遠離家鄉,他便一直陪著父親下象棋。
那時,我住在礦區老舊的六層家屬樓里,每次晚自習結束,理正都會站在學校門口等著我,一聲不響地將我送到我家樓下。畢業時,我考取了上海的一所大學,落榜的理正送我一頂帽子留作紀念。
這是一頂粉紅色的毛線帽,上面有一個絨球,戴上去顯得很活潑。我問他為什么送我一頂帽子,他說:“你戴在頭上就不會忘了我。”
我從夏威夷飛回家鄉的時候,理正在樓下的靈棚里給父親守靈。他還是老樣子,粗粗壯壯,小鼻子小眼,裹一件黑色的大棉襖。見到我,滿臉褶子的他短促地微笑了一下說:“給老爺子磕個頭吧,告訴老人家你回來了。”
我一邊抓住媽媽的手,一邊哽咽地看著靈棚里的父親。父親遺容安詳,就像在沉睡中。母親說,我出國后,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理正張羅,得好好感謝理正才是。
晚上,理正依舊為父親守靈。寒風刺骨,刀子般的風將落雪削成薄片,一直送到靈棚。母親見理正戴的帽子太薄,催我回家里取一頂暖和的帽子給理正戴。我找到了一頂東北最暖和的狗皮帽子,準備交給理正時,母親阻止說:“這是你爸的帽子,哪能讓理正戴你爸的帽子!”
理正一把搶過狗皮帽子戴在頭上,憨笑著說:“我哪有那么多講究,老爺子待我像親兒子一樣,就當我給老爺子戴孝帽子了。”
那一晚,我跪在靈前,理正一直在旁邊陪著。他沒有問我在夏威夷的工作和生活情況,我也沒有向他道謝。
我問理正,老爸生前對我不放心吧?理正說:“可不是,他說你離婚了,連個孩子也沒有,一個人住在國外,將來咋整?”我回復他,聽說你也單身?理正淡淡地笑笑,不說了,老爺子聽到了鬧心。
第二天,父親上路了。
很多人都在為父親送行,在最后為父親整理遺容時,母親卻突然堅持要給父親戴上那副鏡腿磨損的老花鏡。她紅著眼眶喃喃自語:“你爸這輩子離不了這副老花鏡,不戴上它,到了那邊,他連路牌都看不清,該走錯路了。”
于是我向母親索要家里的鑰匙,母親摸索著找了好久也沒找到。明明鑰匙就在衣兜里,關鍵時刻卻怎么也摸不出來。
這時,理正說:“我去樓上看看。”
只見他噔噔地上樓,然后聽見他使勁拽門的聲音。
過了一會兒,當我們以為他已經破門而入的時候,卻見他戴著狗皮帽子出現在走廊的窗臺上,他踩著窗臺,摳著墻體的紅磚縫隙,慢慢地向我家的陽臺靠攏,正當抓住陽臺的一剎那,他的手一滑,便在大家的尖叫和呼嘯的寒風中重重地墜了下去。殷紅的血從狗皮帽子里滲出。
這是誰也不愿看到的悲劇。但不管怎樣,父親與理正的離開對我來說都是巨大的悲痛,那頂絨球依舊蓬松的粉色毛線帽,成了我對他們最深的念想與最痛的牽掛。
父親和理正的葬禮結束后,我給他們各買了一座公墓,兩座墓之間用黑色的大理石砌了一個象棋盤,上面擺了一副象棋。遺憾的是,理正送我的那頂粉紅色毛線帽一直珍藏在夏威夷,如果當時帶回來了,我一定把它放到他的墓前。
來源:曲靖日報·掌上曲靖
編輯:詹宇涵
審核:盧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