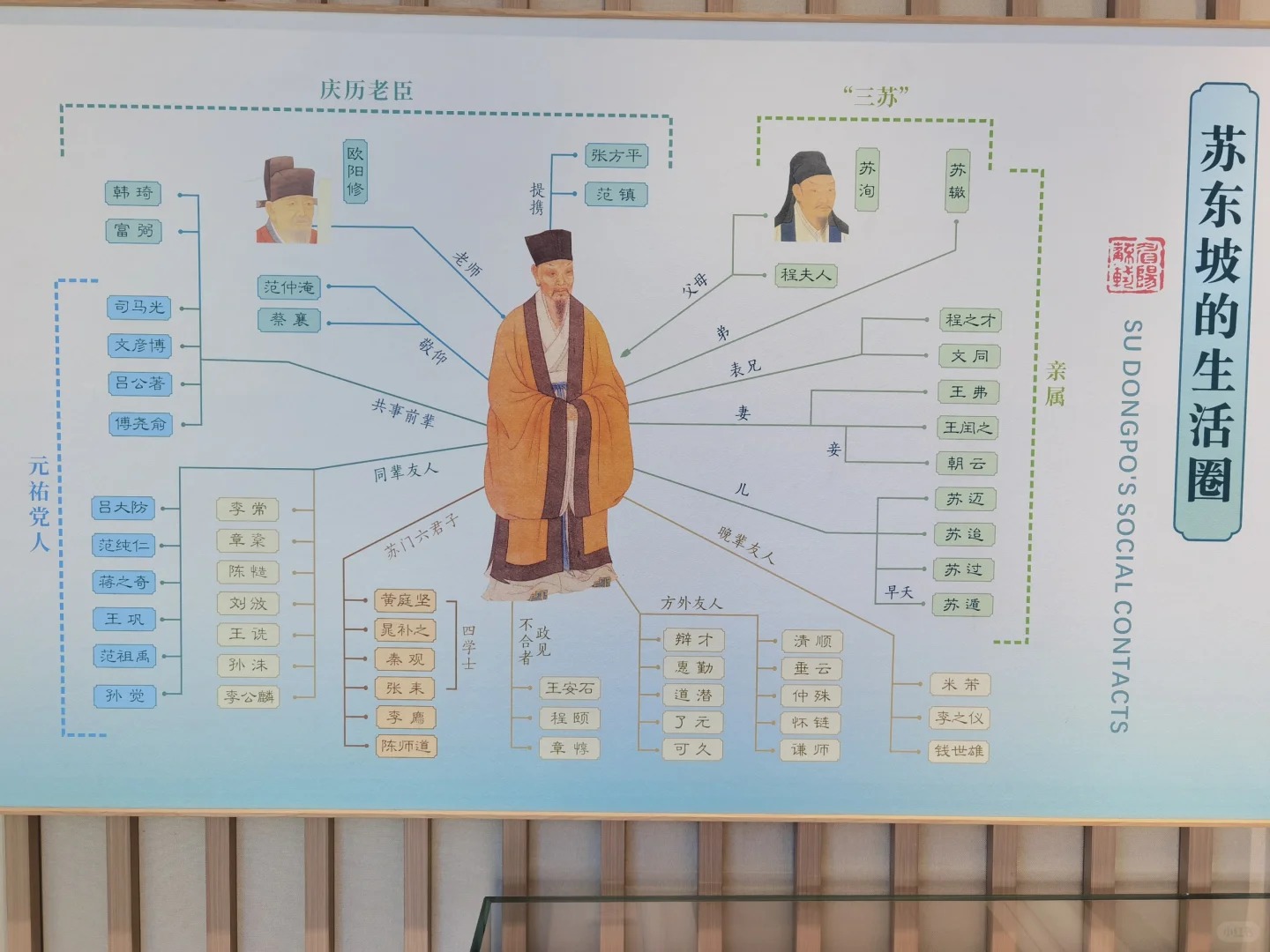#2025新星計劃4期#

元符(1100年)三年正月:哲宗駕崩,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四月:蘇軾獲赦,授“瓊州別駕,移廉州安置”。六月二十日:渡瓊州海峽,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以“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釋然面對磨難。
元符三年七月至九月:經雷州、廉州,沿途百姓夾道迎送,友人酌酒贈詩。
雷州的土地,在腳下竟有種陌生的堅實。六十五歲的蘇軾踏上徐聞鹽場碼頭時,那一陣突如其來的眩暈,并非全然來自舟車勞頓。那是身體對“安穩”的背叛性遺忘。三年來,儋耳的沙地是松軟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時間的流沙上;海島的颶風是搖晃的,連夢境都隨著茅屋震顫。如今大地巋然不動,他的膝蓋卻背叛了他,如同久困籠中的鳥,乍見蒼穹,竟忘了如何振翅。
一直陪著身邊的小兒子蘇過扶住他時,觸到父親臂膀的輕。那不是消瘦,是某種沉甸甸的東西被卸在了海上。行李被官差逐一清點,書箱少了,被白蟻蛀空的不僅是竹簡,還有一段拼命想要抓住“立言”以對抗虛無的執拗。唯有那根黎族少年贈的藤杖,還固執地攜著熱帶陽光的溫度。這一刻,他忽然懂了陶淵明“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的深意——所謂“得所”,并非抵達某個地點,而是終于接受:自己已成一片漂泊的葉子,不再尋找扎根的土壤,只在風中辨認自己的紋路。

故人張逢的接風宴,華燈如晝。緋袍官員疾步迎來,臉上堆著久別重逢應有的熱絡與一絲不易察覺的審度。宴席上,八珍羅列,酒香氤氳,是屬于中原的、熟悉的、精致的秩序。然而蘇軾只要一碗白粥。他說:“腸胃已不識膏粱矣。” 此言輕落,席間空氣為之一凝。這不是推辭,是誠實。海島的歲月,已將他身體的典章制度徹底改寫。粗糙的薯芋、腥咸的魚膾、清冽的椰漿,這些曾為生存所迫的飲食,如今反成了他與自我、與那片蠻荒之地簽訂的隱秘契約。精致的膏粱,于他反成了一種需要翻譯的陌生語言。
張逢在月光下找到嘔吐的他。那佝僂的背影,不再有“會挽雕弓如滿月”的張力,卻有一種被風雨反復捶打后的、柔韌的弧度。他們談及朝堂風向,蘇軾眼中無波:“你看我這副形骸,還能回汴京的棋局嗎?” 這話里沒有怨憤,只有洞徹后的疏離。他曾在棋局中搏殺,如今卻只是觀棋人,甚至看那棋盤,都隔著一層南海的霧氣。與張逢的相見,照見的恰是兩種“幸存”:張逢幸存于官場的小心翼翼之中,而他,幸存于對一切小心翼翼的徹底放手之外。

病,是這十日里最忠實的伴侶。瘴毒深入骨髓,在最為安穩的陸地上發起最劇烈的“起義”。腹瀉不止,他卻在那污穢的茅廁中,看見縫隙里掙扎出的一株嫩蕨,綠得驚心動魄。病榻成了最澄明的觀景臺。他修改《志林》,筆鋒劃過“瘴毒”二字,忽然頓悟:這反復的疾痛,或許并非身體敗壞,而是靈魂與肉身在討價還價——魂留戀椰風海韻的粗獷自由,身卻要回歸中原的秩序文明。這場撕扯,以最生理的方式呈現。
他在驛站斑駁的墻上題詩,手腕顫抖,墨跡卻如老梅枝干般奇崛。“歸路老更迷”,他告訴蘇過,此“迷”非迷失,是迷醉。是了,當一個人走過足夠長的歧路,便會發現,“正途”本身才是最巨大的誘惑與幻象。那些看似偏離的腳印,連綴起來,反而成了僅屬于他自己的、最真實的生命軌跡。墻皮終會剝落,詩跡終將漫漶,但這“迷”中之“悟”,卻如種子落入心田。

更深的觸動,來自那些靜默的陪伴。守關老卒珍藏著他七年前南貶時詩稿的拓片,紙緣摩挲起毛。老人渾濁的眼望著他:“學士詩中說‘身世永相忘’,老朽卻忘不了。” 蘇軾忽然被一種巨大的溫柔擊中。他的文字,他的苦難,他的達觀,并非僅僅屬于他個人。它們已成為他人記憶的坐標,成為另一個生命在荒涼歲月里用以辨認方向的星圖。這比任何廟堂褒獎都更沉重,也更輕盈。
而那位穿越兩月山路、自儋州徒步而來的百歲黎母,奉上一串風干的檳榔。她為的是替病逝的孫兒道謝,謝他教那個渾身魚腥的少年,第一次寫出了自己名字的“魂魄”。接過檳榔的剎那,蘇軾感到一種根本性的顛覆。他總以為自己是文明的施與者,是知識的布道者。此刻才驚覺,真正的教化是相互的。他給予了文字,獲得的卻是關于生命質樸尊嚴的至高教誨。他解下御賜玉帶相贈,老嫗拒收:“黎人土地,本無買賣。” 她留下的,是一個比任何玉帶都更珍貴的理念:有些價值,存在于流通與占有之外,只存在于記得與念想之中。

雷州的夜,海風依舊咸澀。他獨自立于灘涂,望向南方那片已沉入黑暗的巨影——海南島。三年前的恐懼與絕望,被時光熬成了復雜難言的眷戀。他在告別,但告別的不只是一座島嶼。他在告別那個仍需用“建功立業”來定義自我的蘇軾,告別那些糾纏半生的榮辱勝負之心,也在告別“告別”這一行為本身所含的悲情。
他終于明白,人生至為珍貴的,或許并非“擁有”,而是“經過”。經過瘴癘,方知身體并非城池,而是可與自然談判的驛舍;經過離亂,方知功名并非歸宿,心安才是唯一的鄉關;經過生死邊緣的凝視,方知每一次病痛都是生命在低聲重申它的限度與尊嚴。那些最深的共鳴,往往來自陌路人的一個眼神,來自苦難中未被磨滅的純良,來自意識到自己亦是他人故事里一盞微燈時的顫栗。
北歸的路還在前方,更長,也更短。他的身體是一部寫滿注釋的舊籍,每一處病痛都是一個注腳,指向某段風雨、某次離別、某頓粗茶淡飯里的恩情。他不再急于趕路,因為每一步,都是對過往的收納,對當下的諦聽,對終點的預習。

立于雷州陸地,咸風盈袖。忽覺此情此景,與廿四年前黃州沙湖道中那場急雨,竟隱隱相通。那時,我以竹杖叩擊大地,向風雨宣示“誰怕”的倔強;此刻,手中藤杖輕觸紅土,只感萬物皆親,無物可懼。
那時的《定風波》,是一曲突圍的戰歌,是與命運公開的角力。“竹杖芒鞋輕勝馬”,是向困厄展示精神的優越;“一蓑煙雨任平生”,是將苦難主動納入生命版圖的豪邁。字字皆是鋒芒,句句皆為鎧甲。
而此刻,風暴早已不在身外。它已內化為血脈的流速,呼吸的節律,成為生命本身沉默的底色。無需“吟嘯”,不必“誰怕”,真正的平定,是連“平定”之心都悄然放下。那場曾需要以全副心力去對抗、去超越的“風雨”,如今看來,不過是天地一次尋常的吐納,而我,只是恰巧經過的一粒微塵。

步舊韻,賦新境,作《定風波·北歸雷州偶感》:
常羨人間自在天,百越歸來謝華簪。竹杖曾驚滄海水,今看,布鞋微陷舊沙煙。
故友新炊盈玉案,輕喚,一甕煙霞煮素餐。藥灶經年溫病骨,漸暖,春風先綠杖頭蘚。
莫嘆余生多逆旅,且住,此身安處即南山。幾度潮平舟自橫,清醒,滿天星斗落空潭。
黎母贈丸猶帶露,歸去,云輿不必候青鸞。回首向來蕭瑟處,不語,也無風雨也無庵。
“無庵”,是連最后那片名為“超脫”的精神茅棚也一并拆除,將赤裸的靈魂,徹底還予無垠的天地。
從黃州的“突圍之悟”,到雷州的“釋然之歸”,中間隔著廿四載的貶謫流離,其本質是一場從“對抗世界”到“融入世界”,最終“成為世界”的漫長修行。風未曾停,雨未曾住,只是那聽風觀雨的人,心湖已湛然如鏡,倒映萬物,而不留一物。這或許才是生命所能成就的,最深沉、最廣闊的“定”與“平”。